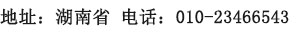梁晓明,中国先锋诗歌代表诗人。
开篇(选章)梁晓明
对诸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又太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海德格尔
13、我遍尝风霜
——我为他的愤怒
感到泄气
他活着已经是一付重担
他还要加上更重的负担
自从初夏在石碑上站住脚,我和他便开始遍尝风霜
每一次远离,车站与度假
惊醒的电话,信,和一切亲切的笑容
在翻手的天空下
风暴与风暴连在一起,但是我和他
难以分开
他和死去的人一起讨论活着的意义
他或者站起身
在新鲜的太阳下指责一筐变质的带鱼
我为他的愤怒
感到泄气
他活着已经是一付重担,他还要加上更重的负担
他穿行在火焰中,他两眼射出纯粹的黄金
他喜悦时手捧着鲜红的苹果
谁在吃苹果?
苹果一旦离开枝头
它就将落入人类的命运
这样,我不得不再一次寻找发芽,我生的欲望
烈火的大笑与水中的拯救
为了他美好的双眼
我沉寂
无语
自从初夏在石碑上站住脚,天空不再说话
他藏起了喉咙
他将他的大门朝我们关闭
走下去
这种磨难,带着磨难的心,走进宝塔
苍鹰的爪,大海与篷帆
一次次远离与团聚,梦想
和半夜停电前最后一盏坚持的孤灯
走下去,一点点流露出他的感情
好象眼中射出的黄金
既然他与我已经落入历史的手中
在他斑驳的墙上
只能走下去,从墙中走出
被一扇门关闭只能试着走另一道门
但是地点与终结,是谁?
是谁呢?
将丧钟敲响着
将无尽的空白预先刻满在最高的墓志铭上?
14、石碑上的姓名
石碑上刻着字,你在哪里?
你的手是肉
你的泪是水
你向风赞颂的歌
风早已将它吹入泥土
你站在碑前看
你靠着碑文想
你的一生是鞋子的一生
是世界安排的路,是世界制成的鞋
在世界的梦想中你走到了尽头
你依恋,你回首
已经没有边缘,可到处都是边缘
已经没有了生长,可到处都是生长
石匠在刻你的碑
石匠在刻你的字
你的姓名在石头上看你
你在战胜在碑文里送你
你缓缓起飞,你到底在哪里?
那人们最为畏怯的生命
你却在心中默默地赞美
你观察你的手
你分析你的泪
你将唱过的歌曲一唱再唱
你难以离开,你难以忍受
但永恒的是轻风,永恒的
是四季
在世界的尽头鸟从来不飞
在世界的尽头我没有消息
15、荣耀
语言离我而去。今天开始
我从这世界上争取到的荣耀
如青瓦上纤细的一缕烟
离开我
轻轻散去
作为一个人,我从何处得到荣耀?
我有什么荣耀可以值得
对人谈起
浪漫的树叶想用绿色染遍秋天
但是积水
碰到冬天就开始积冰。
从何时开始,我们的眼睛有了一个结晶体的别名?
我们的眼睛开始结冰
我们的伟大
终于建立在狂风的基础上
从此之后
我的泪水将对谁而流?我将对谁
说我心底心酸的爱?
我活着,然后去死
很多人活着,接着去死——
为得到一点多余的住宅
如一捧飞灰想占住时间,想在风中
更久的飘摇
但是下坠,这泥土的宿命
谁在说希望是太阳的光辉?
我们还这样从一个家门到另一个家门
从一座台阶到另一个台阶
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地
不断转换着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女人
用她们的身体和爱情的家
不断提醒我们的前进
但是
我们的眼睛已经结冰
我只是这样一个人,我又怎敢大声的谈起荣耀?
我又怎敢对人类问一声
将在几时结束?
我们重新过一遍我们的一生
16、雪
比疆界更远。大雪
深深下落
他以轻松的步伐
走遍乡村、城市、烟囱和树杈
每年的最后
雪从空中向人间下落
雪以纯白飘动的步态告诉世界
他活着,始终呼吸着
直到死亡来临
——大雪向大地全面服从。
从不大声呼喝,只是轻轻讲述
在时间最后的广场上
象一个奇迹,死过的大雪啊
经过欲望的六月,竭尽表现的
阴险春天
放肆劫掠后
衰残的秋季
又一次
他深深下落在悲痛的大地
洁白一片
接着另一片,因肮脏而死
然后
又重新来临
是这样坚定活着,并且
始终呼吸着
从不大声呼喝,只是轻轻讲诉
大雪向大地全面服从
开始于空中
再走向大地
在人类的生活中他最后完成
比疆界更遥远。我站在街边
我看着大雪向我下落
我想着宿命,我已经是另一场牺牲的大雪
在时间最后,我将痛哭
流泪
因为无限的大雪在说:
他就是我的未来,目前正是我的现在
17、向下看
向下看,与鸟一起生活的人
春天离他们越来越远
我看着花开,我看着他们在流水中
在漂撒的羽毛中将一生度完
来自底层的草最终在泥土里
落入归宿
泥土是他们的根,他们的家
与灰土一起将宿命低吟
成绩与清明一起下雨
正如相反的鲜花,他开花在枝头上
正如鸣蝉歌唱在高处
鹰将道路铺开在天空上
我看着这一切发生
我又转身走开,我微笑
我不表态
我把手放在了季节的门外
18、好消息
好消息被你带进明天
我风尘的战袍再一次黯淡,再一次退色的
我的眼睛
向胸前收拢高飞的翅翼
我降下来
在急促的钟声里将灰烬掸净
我穿过石头,黑烟和高塔
永恒的旗杆上
我浸透了冰霜
我降下来
我降的还不够
好消息深埋在各户人家
馨香的好消息是低矮的灯盏
我降下来
背后我盖住了明天的光芒
19、进入
那在风中久藏的,风必将使他显现,
正如一滴水
他来自大海
他的归宿与泥土为伴
我经历过风,我深入过最早的语言
在风中歌唱的
风将最后为他而歌唱
我领略过这一切。我沉思的手
在不可升级的高地上停留
在闭门不出的庭院中开放
或者布种
好象是最好的梦境为眼睛打开
为城堡打开
为最迟的旅行者卸下了负担
我与风一起深藏
与歌一起高唱
在棉花地里我深入过季节
旺盛的季节
为落叶而鼓掌
为丰收而站立畅饮黄酒
最烈的黄洒也是我最不可忘怀的回想
我一点点记叙
我一点点遗忘
我一点点走入我生命的中途
20、漫游
我身上落下了该落的叶子。我手下长出了该长的语言
我歌唱
或者沉思
我漫游,或者在梦境中将现实记述
我已经起飞
但飞翔得还不够
我低下头
我在褐色的泥土中将水份清洗
钟声不响,我的歌声不亮
正如一轮太阳使夜晚向往
我跟着一只鸟,我观察一群鹰
我在过去的传说中展开了翅膀
是告诉你的时候,我在说着故事
是繁盛的开端,我在倾听着寂静
好像是一种光
我在光中回想
在最大的风中我轻轻启动着双唇
没有字
没有让你领悟的通道
已经落下了叶子,但落得还不够
在应该生长的地方
我的飞翔在飞翔中静止。
21、秋风
就像一阵秋风,就像一场大雨
我转瞬离开又迅疾来到意外的河边
那是苦干的八月
黄金的太阳正敲打它那不破的铜锣
覆盖着荷花,最美的少女
就像一场大梦将人生改变
我看见季节的衣裙总是比我
更早的抵达
那些星星的语言,歌声的大姐妹
那些将黑暗从瓦罐底下挖出的叙述
我在八月被深深震动
沿着白杨树拐弯
大水也跟着前进
在水中我曾经是自由的一尾波漪吗?
我有可能在自由中驻足过一刻吗?
在八月的大水中
我是否已被怜悯托起?是否已被更大的狂风
将我的口粮与我分开来?
使我最旺盛的手势落入跟从的
不会将道路一分为二的
棉花的絮语与狗眼的狂喜中?
是的。我的心被天空定音!
被嘈杂的蚂蚁向低暗的家中坚持搬运
最嘹亮的童年被青春撕碎
如一片单薄的风,如一列火车
在期望的行进中
将往事丧尽!
之后,我落入了灰尘
我在陌生的水中无视呼吸
我已孤单,
我还孤单的不够
正如一场秋风,正如一场
逝去的大雨
22、树的插曲
在诞生之前我就在等待,一个人
越过茫茫人海终于来到我面前
他伸手捧起我,他将我插入
温暖的泥土
我伸枝展叶,这时我开始在空气中等待
我在街边、花园里,或者荒野
孩子、成人,甚至野兽露出友善的双眼
我开始粗壮,这时我等待各类啼鸟
它们将叫出我心底难言的喜悦
之后我等待下雨、惊雷、太阳和云彩
我开始衰老,我被焚烧、伐倒
或者被拖到狭窄的后院
被一个人用斧子从中间劈开
我死了,我又回到诞生以前,我重新等待
哀伤、喜悦、痛苦、兴奋
他们都不重要
我是树,等待便是一切
我是树,或者我就叫等待
23、下面的预感
我们的生活象冷清的黑夜从眼皮底下翻起
置身在麻雀
轻佻的
四处乱停的风中
属于我们的日子
它坐在一只大木吊桶中
向命运难测的深井中坠落
向上的生命和向下的流水
友谊在打滑的卵石上诞生
可是心灵底下的希望
寂寞中太阳一样生出光芒热烈的翅膀
等到时间敲门
等到时间插进另外一只手
所有丰富的脸庞全都变成最初的一张白纸
谁不苍白
谁就与人类分开了归途
我对风说爱
我对水说坚持不动的信心
可大街上的人们四处走开
他们低着头
惊喜地寻找最近的通途
我知道我是一撮灰
旺盛的年轻烧剩下的一撮灰
我站起身体
从地下的灰中
我端出我的笑脸
笑脸是我活着的唯一证明
可世界说灰尘是大风的唾液
24、允许
——允许我的思想开始流动,接受风
接受你内心善良的大雨
允许我的精神在风中坚定,在歌中胜利
在最小的石块中说起永恒
允许我在树中生根
在广大的荒漠中我寻找到水分
允许我第一口喝下这神圣的露珠
你双垂的眼帘
允许我走过你的膝前,象一个人
身上是坚硬的白骨头与
太阳上笔直流下来的血
允许我飞过你的门楣,堂前
如夜晚的流萤
因为你我发光
我展翅
在你的时间中我得以进食
允许我的思想开始流动,接受风
接受你内心善良的大雨
让我光辉,让我脆弱的双脚
抬头升起来
在众星之中让我从你得到喜悦,欢笑
最美丽的女子
与河流碧蓝的大腿
让我生下的孩子使我宽心
幸福绕膝
与悠长的回忆
让乐观象黄金一样被我领受
从你智慧的大手中
让我在无家的人群中得到一个家
得到一把开你的钥匙
并且允许我随意地出走,碰壁
直到在浪费的血中再度将你认出
象衰弱的草再度认清阳光
允许我向上站起
象虎一样生长
允许我的双眼色彩斑斓
在我的死亡中你永远不死
因为我的逝去你再度扩宽了永恒
梁晓明和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杭州,年。
现实与超现实:梁晓明诗歌中的自我□刘翔
导言
梁晓明的诗歌无疑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成就,他的《各人》、《玻璃》、《开篇》等都是当代诗歌的名作,但在这个集子里都没有收录,他收录在集子里的大多是一些早期的作品。自我的、浪漫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蔑视生活现实的诗,是他的创作的一脉,但现在“那种独立和恣肆狂野的气象好像已成上辈子的世界,我甚至能感到它已独立的渐渐的离我而去,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但在骨子里,梁晓明还是依然故我,仍然渴望“披发赤足而行”(他说过“披发赤足而行,明显地有着蔑视生活的态度的生活”)。只是现在,他似乎更多地企图去承受现实而不再仅仅是蔑视现实。“现实把头摁到大地上”,是的,社会现实总是以铁的意志制约着人,可是如梁晓明所说“我的诗歌哲学总是忍不住要落到快乐与希望的字眼上,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的理由”,沿着自我,梁晓明展开他的世界,沿着自我,梁晓明力图进入超现实的世界,而现实仍然躲藏在里面。现实和超现实其实在梁晓明的诗歌世界里是一个复杂的图景。在这本诗集中,我们看到更多是一个个昂扬的形象,但也在里面呈现着一种挣扎、突围甚至挫败感。一些人,包括梁晓明自己,认为在他的诗歌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表现为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有理想情怀的诗(代表为《歌唱米罗》、《告别地球》到《开篇》),而另一种是则是灰暗地表现人生窘境和极端行为的诗(代表作是《各人》、《玻璃》等)。但其实这两种倾向是交缠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尽管似乎比较多地是涉及前一类的诗,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梁晓明的总体创作倾向。
最早醒来的光芒: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像大多数年轻诗人一样,梁晓明也是从浪漫主义起步的,他最早的偶像是惠特曼。当意气风发的他背着惠特曼的诗集来到城市的时候,他感觉是来征服这个城市的。梁晓明肯定被那个在惠特曼诗歌里隆隆作响的“自我”所震撼和唤醒了。这是多么庞大的“自我”,如此豪迈和激昂。
惠特曼――美国现代诗歌的源头,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伟大的创新者,旧传统的毁灭者,偶像的破坏者,《草叶集》中最核心的诗歌就是《自己之歌》,是“我自己的情感和个性的其它方面的表露――它从头至尾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即要把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我自己,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人),不受约束地、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下来。”抒写自己,是惠特曼的一贯主题,也是梁晓明诗歌创作的一贯路子。来自惠特曼的影响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梁晓明通过学习很快掌握了更现代的诗歌表达方式,这种影响是精神气质上的,是一种契合,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从这种浪漫主义的天性和理路出发,就不难发现尽管现代诗人大师众多,他为什么特别喜欢圣琼佩斯、埃利蒂斯,而在中国的古典诗人中,他又特别对李白、苏东坡津津乐道。
但要说到和梁晓明的创作之真正的休戚相关,则还是首推“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流派,但有人却也把它称为是浪漫主义的尾巴,一条强有力的尾巴。在一首名为《超现实主义》的诗里,梁晓明这样写道:这些不大吃饭的人近来和我谈纽约的广播飞机是鸟的爸爸天空是日本昭和的微笑我想到一本书里我的名字三次出现梁晓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裤子是不是裤子?我为什么要长一双很漂亮的眉毛?坐在床上担心广东担心被单是另外一个我突然跳起来和我谈苏联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浪漫的、飞扬的自我,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离开了(“超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是深入了)现实。有时,梁晓明被看作是八十年代“南方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一,所以,要了解梁晓明的诗,有必要了解他所创作的背景。“超现实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艺思潮之一,最早兴起于法国它对诗歌、电影、美术等艺术的发展都曾经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超现实主义”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潮中被介绍到中国,对许多中国诗人产生影响。首先,“超现实主义”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呈现的,在艺术观念上给人以最有效的影响,在艺术形象上给人以最直观的打击。布勒东、艾吕雅等正统“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佩斯、夏尔、埃利蒂斯、聂鲁达、巴列霍、帕斯、索因卡、阿莱克桑德雷、狄兰托马斯等所谓“边缘超现实主义”诗人,以及米罗、达利、唐吉、德尔沃、恩斯特、马格利特等“超现实主义”画家,对当代诗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超现实主义”有几个特点是特别新颖的、引人注目的。第一,梦。它承继弗罗依德的学说(但并不严格),对“梦的领地”进行孜孜探寻,梦吸附了个人的无意识,也如荣格所说,它也是集体无意识的深渊,“在梦中,我们就披上了居住在原始黑夜中的那个更普通、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的外衣。梦正是产生于这些连成一体的奥秘之中”。布勒东说:“梦幻,作为被压抑的世界的象征和超现实的范畴,一种认识方式,甚至可能是最有启示性的精神活动”,正统的“超现实主义”的诗类似于梦呓,它把梦中的形象翻译成词语。第二,反抗。“超现实主义”自命是一次革命,对父权社会的反抗。在他们看来,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的一个方面。反对权威,一种开天辟地之感,是许多“超现实主义”的态度。在梁晓明的诗歌与言谈中,它也是一直存在的。第三,“超现实主义”诗人追求语言的神奇性,他们的语言特别自由,他们认为,用通常的语言很难表达梦幻世界,因此,人们经常要赋予日常语言以奇迹,“语言的神奇性”,是这些诗人一直探求的。这种语言是形象的,类似于舞蹈,梁晓明在超现实主义阶段的诗歌,在语言和意象上,都强调舞蹈性。他说过:“我希望诗歌像舞蹈。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曾经想象和努力地去做到:诗歌就像舞蹈演员踮起的足尖,那足尖点在舞台上的一连串舞步便是诗歌,你由一个舞点不能彻底完全的领悟诗歌,因为它仅是一部分,你必须看完整个舞蹈,甚至整个舞蹈看完了,你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它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注意:它只是引领你,暗示你,启悟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边缘超现实主义”诗人使这个运动产生了最大的效应。“超现实主义”诗歌并不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兴起以后才有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几种情况,第一类,是先驱者,像佩斯就是一个先驱者,“他远远看起来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第二类,似乎是平行的,比如英国的狄兰托马斯、德国的萨克斯等,在语言风格上与“超现实主义”诗歌有相近之处。第三类,受到影响但变化了的。
这类是多数,这些诗人在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影响或激励后进行创作,如希腊的埃利蒂斯把“超现实主义”看作是欧洲大陆的最后一点氧气,但他抛弃了“自动写作”等“超现实主义”的教条,与他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的阿莱克桑德雷等。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西方世界掀起的文化运动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解放力量,逐渐成为了第三世界诗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武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边缘”意义的“超现实主义”,他们适当采用“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来控诉殖民文化的后果、反映自己民族的“神奇现实”并力图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聂鲁达、帕斯、巴列霍、桑戈尔、塞泽尔、索因卡、沃尔科特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聂鲁达、埃利蒂斯和佩斯好像是梁晓明最钦佩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一次梁晓明写到:“我又想起聂鲁达,当马楚比楚高峰矗立在他面前,当他写下‘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每一块石头都溅出回声’时,我们能说,你聂鲁达又不生活在马楚.比楚山峰下。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只能和聂鲁达一起攀登,一起感受,一起扣问和追索,一同经历死亡和最后的歌唱。”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是梁晓明读得最多的诗篇之一,这是一组伟大的现代颂歌,又是“超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它也是一组自我之歌,“那个真正是我的人,那个确曾是我的人”,那个本质的我,超越了平庸的现实,在歌唱,那个诗人是神奇的:“我张开嘴,大海便高兴”,他放声高呼:“那是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而佩斯,这位当代诗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只写了十多首诗。他认为,诗歌是一项、首先是一项天才的事业(这个观点与早期梁晓明的意见完全一致)。在他的《远征记》里,他写道:我建造了我自己,用荣誉和尊严我在三个重大的季节里建造了我自己它前途无量――这片土地在它上面我制定了我的法律
在这里,诗人是君主,是立法者、征服者、城市的缔造者、美的发现者。在佩斯的诗里“满是最高级形容词的长句,具有古希腊歌队所特具的崇高气质”,它带着传统咒语的力量,它是精美的颂歌,也是肃穆的咒语。最令我们惊叹的是其中充溢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自豪。梁晓明年4月写有一首题为《读完圣琼佩斯壁灯点燃窗前沉思》的诗,它似乎并不太像佩斯的诗,但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和开阔性:太阳这幅棉被掀开我的头发时,正好从砖瓦间伸出舌苔正好指甲在被人议论,正好我派遣我的脸去菲律宾游览美景热带像一条带鱼游进我的眼睛里时正好从钟楼上伸出屁股光滑可爱,带着青斑,好像刚从大麦的麦尖上生长出微笑与青铜的宝剑当悲伤点燃房屋的寂寞,孤独绕着我的门楣舞蹈,把脚尖踮着我的耳轮唱歌时我已经波浪一样关心起水面把快乐羊一样向世界赶开我沿着煤气管道走进各个家庭,把他们鞋子里的黑暗全部倒光在一小杯酒中我站在岸上呼吸中花朵盛开蜜蜂在窗帘上跳舞光芒水一样漫过大桥我手掌翅膀一样向天空张开
自由与纯粹:米罗、米罗
梁晓明在一篇文章中说:“霍安.米罗的‘一滴露珠惊醒了蛛网下睡眠的罗萨莉’及‘小丑狂欢节’时,我全身都被震动了,当我看到肢体也有它自己的语言,而小虫子、凳子、椅子、灯管、手风琴、铲刀、所有的动植物,甚至各种器具都竭力地扭动起自己的身体、在竭尽欢乐的舞蹈时,我当时就想到,这就是我的诗。在这种理念的支撑引发下,我从年一直写到了年才终于写完。像《歌唱米罗》、《读完圣琼佩斯壁灯点燃窗前沉思》、《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及《给加拿大的一封信》等”。可以这么说,“超现实主义”艺术附体在米罗一个人身上,对梁晓明的作品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在梁晓明的诗里多次出现“米罗”这个词,这是一个人,一个画家,也是一种精神、一种自由的象征。《全世界都在等待阳光》这首诗的意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米罗的画:
我就悠闲自在地走上阳台,想像自己在半夜
悄悄跨出栏杆,从六楼看自己的身体
像一架摔裂的机器。
大腿这个零件便倒挂在围墙上
和走拢的星星们一起叹息
我眼睛鸟一样停立枝头,
我左脸上蝴蝶纷纷起飞
梁晓明还写过一首名为《向米罗致敬,半夜我披着窗帘起飞》的诗,这也是他比较著名的一首诗:
天空飞翔我的脸
我眼睛是星星照亮的,
在陶罐上发亮的刀剑中
我的指甲因为太阳而日夜生长
山坡向大海张开他倾向唱歌的嘴巴
一万里的喇叭与飞出去的鸟
我搭手在栏杆上细数去而复归的羽毛
沟壑扩展我的家,
当手掌离开钥匙
大雪老远就击打着拍子
把指头按满在我的窗子上
半夜我披着窗帘起飞,提着泉水的灯笼
天空回转身惊诧我头顶跳跃的黑发
我浑身的瓦片都点亮着蜡烛
墙壁竖起了道路,帽子飘飞起旗帜
梯子向上升起我的脚
一首纯粹的诗在风中挽着苹果出现
在翘望的树林与太阳高高飞翔的下巴上
灯罩与音乐歪倾着脸
默默坐在大麦丰满芳香的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米罗的创作,从而企图找到与梁晓明诗歌的契合之点。“超现实主义”绘画和诗歌一样,都是这个运动产生的巨大成果的领域(“超现实主义”在小说、音乐等领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绘画产生了契里柯、卢梭、恩斯特、米罗、达利、唐吉、德尔沃、马格利特、高尔基等一大批大师,但为什么独独米罗最受梁晓明青睐,这个问题可能连他也难以回答,其实他也很喜欢达利和马格利特,但在诗歌和文章中从来没有提及。我想,在偶然中也有一些必然,我试图进行一点分析。契里柯显然是很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但契里柯式的逻辑性非常连贯的非清醒世界(契里柯对梦的洞察),加之形而上学的美学,沿袭罗马时代的画家的风格以及厌世主义,显然不太合梁晓明的味口。而达利的癔病式的偏执,他的画作中那些荒谬绝伦的、狂野的幻像,那些用像照相一样的、学院的技术画出的真实得令人可怕的世界图景,尽管震撼了梁晓明,但却也并不他的最爱,同样,卢梭、马格利特这样的“逼真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场景可能由于缺乏一种年轻的乐观主义者所要求的纯粹性,而没有成为影响的中心。
考量米罗的伟大创作,至少有几点是值得
因此,诗人只好“告别”:
太阳每天摸我的头发,
月亮每夜制作梦想
我敲锣打鼓欢迎飞翔,
仔细观察老鹰的翅膀
并在心中涌动起“英雄”的梦想,那是歌,那是如此美妙的歌:
只有歌声向歌声表示向往
波浪就等于手掌一样
只有海洋向海洋演奏天空,
桅杆便竖起衣领希望
让光芒都流到栏杆的背上
让地球像一张太阳的嘴巴
当雄心被寂寞的外衣引诱
在大脑激荡起锣鼓的家乡,
当大鹏又一次飞过我的头发,
麻雀像我穿破的短裤
看自己像看一棵路边的梧桐
叶子是一张时间的笑脸
蚯蚓在地底下运动
它和泥土相亲相爱
春天蝴蝶又穿上花衣裳
是啊,这是如此动听的歌曲。梁晓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赞歌作者,他内心被这种东西所吸引。但仅就赞歌而言,他所礼赞的对象是有变化的,最早是异国情调,后来是吟颂所有飞翔和舞蹈的事物(《歌唱米罗》、《告别地球》等),然后开始歌唱大地――故乡与亲人(《敬献》),最后他把天地作为完整的世界景观,吟唱歌唱天地神人共有的奇迹(《开篇》)。《敬献》是梁晓明的一组非常重要的诗,它在梁晓明的赞歌系列里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诗人曾经这样写道:“把天空放下,我又被大地吸引”,是的,这首诗写于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一段极为灰暗的日子之后,这组诗可以说是一种疗救与康复,相信在写这首诗时,他带着一种幸福感。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乡:
太阳将走远的人们一一唤回,我的身边
草地和悬岩闪闪发光,
香料使一座小城茂盛
大道走向南门,火焰将童年照亮
他们在白纸上写满了波涛
他们在岸上开口倾诉
一片月光将所有的家庭插满鲜花
诗里面有一位这样的父亲:
他的双手抚遍了宝剑,他眼睛的光辉
在宝剑的光辉下将禾苗看遍
将每一块庭院的空间丈量
他宽头的皮鞋梦想又一次
从咯吱叫喊的阁楼下走过
抽屉深藏勋章
他喜欢在风中乱走,在风中,
他张口就出现一条大江
在早晨的风中,他宽大的裤脚呼呼有声
大雾没有解决
他的睫毛还没有闭上
可是,尽管是“敬献”给别人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梁晓明还是以很大的篇幅讲述了自己:
那个简单的男孩,弄堂的鄙视者
谁?把最初一张灰色的纸牌
高举着越过梦中逐渐开阔的世界
把最初一滴玻璃的露水递到他手上的
又是谁?那个漂亮的卷发少年
在舞台上将手风琴的音阶占领
将他满头的热情挥洒在每一张翘望的小嘴上
……我和时间把日子分隔成赞颂与承受
走这么远,我站在自己的堤坝上
我独自站到自己的高塔上
手里拿着一柄小刀
为树叶和孩子们亲切握手时
唱出的歌曲
在他们背后
我终于说出了太阳和我姓名中天空的节拍
对梁晓明而言,《敬献》确实是敬献给故乡和父亲的,但同时也是献给自己的,献给失去了的童年,献给那个“漂亮的卷发少年”初次展翅呈现的热情和光亮。在一种充满现代感的语言中,他伴随着手风琴声,带着乡音赞颂着。他回到了土地,但依然在心中回响着天空的节拍。酸、甜、苦、辣:超现实中的现实在一些早期的诗以及梁晓明对诗歌的表述中,他似乎竭力回避现实、贬低现实,一个“弄堂的鄙视者”,一个世俗的反对者。一度,他说过:“诗歌与人们的时代已呈背离的状态,我们的社会生活与行动也早已摒弃了诗歌的心情与标准,当人们的眼睛开始朝向现实睁开的一刹那,诗歌便被弃绝了。追本溯源,浪漫主义的诞生,与人类生活和诗歌的分离有着密切的关系。”“披发赤足而行,明显地有着蔑视生活的态度”。是的,一度,他认为,他的生活,至少是他诗的生活可以回避灰暗的现实,呈现一个更有激情的、更丰富和纯洁的世界。所以,异国、古代、童年、梦境借想像滑翔,并在白纸中涌现出来。但现实,一种把人摁在大地上的力量还是在背后制约着人。一个宿命的万有引力把人五花大绑在阴暗潮湿的地上。其实,梁晓明一直没有生活在顺境中,他不是时代的幸运儿,他从小镇来到城市,但这个城市并没有欢迎他。依靠一种乐观和自信,他才在压抑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诗歌对他而言,是惟一的氧气。他在其中呼吸,在其中呼唤并找到自我。赤足披发而行、翘望天空、披着床单飞翔,都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在一种自负和蔑视中,他承受着并不想承受的灰暗的生活。他期望“让狂妄像一只破茶缸,让幸福像一条脏短裤”式的恣意的生活,可是,生活还是在背后,作为一种诗意的反面而存在着、控制着人。《各人》和《玻璃》都是反映现实的冷漠和残酷的一面的,《各人》像是一首“生活流”的诗,梁晓明在诗中的语气迹近嘲讽,《玻璃》比较复杂,在自虐中深处涌现了近乎圣洁的力量。这都是梁晓明自己所认为的“另一种诗”,他诗歌与性格的另一面。其实,他并不是总是分裂的,在很多作品中,现实与超现实是混合在一起的,被他所蔑视的现实生活甚至在赞歌中也会泄露出来,是的,一个被扼住的歌喉最想唱歌。
尽管我们说梁晓明主要是一个赞歌作者,但他也确实写下了足够阴暗的诗句,“幸福来到我身上一秒钟/幸福又抬起别人的双腿”,“想起爸爸的一根棍子”,“办公室像时间一样脱我的帽子”,“你站在门口/你不进来你这只蜘蛛/老想把别人抓进你网里去”,“那制造垃圾的人/是我的邻居/在半夜谋划我围墙的高度”,“红灯指示生活”等等,都反映了现实对心灵的压制,下面的几段诗也很好的反映他的心境,在总体的超现实的情景中,这种阴影特别触目:
我的背后好像有扇门
我骑车从大街上拐弯的时候
好像有支枪正透过玻璃瞄准我
好像我后颈上就有枪口
每次穿裤子总感觉什么地方有枚图钉
总想把手上的黑皮包甩掉――《背后》
有一只皮包老想装我
有一张布告老想抓我
有一只鼻子老想气我
想叫你走出我的门槛
想说我自己是柄旧拖把
永远被别人捏在手上
这个城市像只大烟灰缸
谁的烟蒂都想往里扔――《我感到我一直是块毛巾》
他从月亮的瓦片上走近广场
他们在疯狂的弹着吉他
嘴巴在歌唱
桌盘上剩下来的鱼肉和菜汤
苍蝇和麻雀都在飞翔
看--甜蜜的电影,血液和眉毛一起鼓掌――《我必须永远沉思默想》
但在梁晓明早期最好的诗里,不再是光明与灰暗、礼赞与咀咒的双重对立,而现实本身:充满了酸、甜、苦、辣。《忏悔诗,杭州的一次酸、甜、苦、辣》是一首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诗,是生活的复杂镜面的奇异映射。这里有“超现实主义”、爱情、弟弟的疾病、生活的阴影、变形的工作场景、污秽、单纯、放浪、桎锢、理想主义与残酷的自虐等等:
那次我把脚试着伸进糖纸,
我把我的指甲一片片揭下来,
我要看白帽子里面的那些黑发
我把嘴唇贴在她额上,这是第一次,
几块石阶上人的声音在门口点灯,
我像只大狗熊
我跟你说,那是轮子的错误,那是锁的错误。
那是蚂蚁的脚,
我轻轻对你说,看,门外是一片晒谷场
我的手指从香蕉边滑下,以后羊群见我就逃,
我本属兔,我趴在墙头悄悄窥视洗澡的白云,
我不敢喘息,一辈子我将这样死去,
一只臭虫,八只脚,一件棒针衫
黄色勒紧我的锁骨
打字架打字夹我把袖套脱下来,
窗外有船向伦敦驶去,铁锚从我耳朵里拔出,
扶着栏杆的手,许多瓦片
围绕着我的脚跳一种非洲的抖肉舞,
我永远是裤子,被枯干的树枝举在头顶。
北风在我的头上倒酒,我的脸上都是呕吐物
巴拿马桑巴悠扬的五步曲,在圆桌边
我不敢看朋友们的红光,他们的脸膛
浸着啤酒我走出门口,
三个男人围着我要票,一大群人的
眉毛突出,我往墙角蹲去,
我又跳上单杠我要逃,
我把我的昨天浇上柏油,我爬上八楼顶,
从一只袜子里往下跳去,
以后我永远在空气中行走
你好吗?一辈子你是我惟一的红寺庙
以后他在筷子边抽烟,或者在铁栅栏前
等待弟弟,那只电话永远使他难受
声音永远抓住他的脊梁骨,医院像只鸡
每晚啄他后脑上的那块疤
他最后在脸盆边想念双层床,
想念别人的大衣挂在你雪白的蚊帐上
他最后死在铁轨上,手臂像木头飞向菜田
结论:“我和时间把日子分隔成赞颂与承受”
梁晓明的诗歌是他自己的“自我之歌”,他一直在变化着,甚至在同一个时期也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所以,随着对世界的认识的加深,他的诗歌也从原来的抒情、浪漫、快节奏向着慢节奏、沉郁发展,他的诗观也随之改变。在《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一文中说:“我忽然想写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一种完全是由内心在说话的诗!它不同于情感说话的诗。情感说话的诗,在我看来,忽然觉得是那么的轻率、毫无意义和缺少价值。”“所以,我此刻也反对辞藻华丽的诗,那是制作。还有浪漫的抒唱,那是人生的奢侈与浪费和泡沫”。“我需要在诗中出现的是一整座实在的山,一片粗砺的石滩,一间瓦房,一盏灯,一座充满孤寂骚动和冷漠的城,一整个大陆和一个人……他们在人的生存经历中必然是切实存在的,每一物体都必须独自领略过风吹雨打,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段生命的呈现。‘让意象在一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上各自发光’”。而在《九句话》中,他也说:“我希望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艰难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串血,一滴泪,一段梦想,叹息和惊醒,它必然充满沉思,向往,深入人心和现实存在的反映.它是生命内在的视野,是一种经历,体验,观看的沧桑与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开阔新的存在与启示.”“我现在反对辞藻华丽的诗,那是制作.还有浪漫的舒唱,那是人生的泡沫.最后是才华横溢,这个词误导和害死了多少本可以成才的青年诗人.”。确实,这已经和过去的诗歌观念有天壤之别了。梁晓明的个性里有极端的因素,所以,他的断言也有极端之处。而翻看他的诗集,他的诗作有极端的抒情,也有极端的叙事,有极端的浪漫,也有极端的残酷,有极端的超现实,也有极端的现实。当然,更多的情况是更复杂的,在抒情与叙事、在浪漫与残酷、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一个人的诗观不能完全地贯彻在创作中,一个诗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诗作。所以,我没有听信梁晓明早期的浪漫主义诗学和天才观,也没有完全听信他后来的反浪漫主义诗学与反天才观。其实这两种东西一直是他血液里面的两部分,时而融合,时而纷争,但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消失。
自我,是梁晓明诗歌的主导动机。这个自我在时间中漂浮,变幻着自己的形象。我们在前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展示作为诗人梁晓明的自我的各个方面,而在文章的这最后一节,我期望有一个更凝练的表述。我相信,正是这个在诗歌中得到再生的自我,在自我的分裂和团圆中丰富着自身。那是两个自我,一个浪漫一个现实,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一个向往大海一个在孤独中自虐。那个浪漫的自我那么恣意地生活着,他说:“我本属兔,我趴在墙头悄悄窥视洗澡的白云”,“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
闲暇把脚掌插在云彩与云彩中间,听阳光水波
耳边唱歌,看鸟翅膀拍打姑娘翅膀
这是多么昂扬的自我啊:
我炊烟一样舞蹈起自己的大腿和肩膀
波浪一样我放纵起自己的肋骨和胸腔
教堂一样我欢迎灰尘和空荡荡的奶牛场
和桅杆一起朗诵屋檐,
和猎枪一起梦见电影院
在早期梁晓明的诗里,“梁晓明”这三个字作为姓名动机,常常出现在诗中,比如《等待陶罐上一个姓梁的姿态出现》这样的诗,以及这样的诗句:
如果我吸着烟,一脚跨到
空气与手掌的栅栏外面
如果我忽然站到墙上,伸出手指
点向美国我推开门,
看见梁晓明这几个字顺着阳光的台阶
笔直走到头发的屋顶上
甚至诗人的自我与诗歌是具有同一性的:
诗歌沿着我两条眉毛向后脑发展
诗歌拥抱我每一根头发
在每一块头皮上它撒下谷种
诗歌在我的鼻孔里醒来
醒来就迅速张起蓬帆
顺流而下
诗歌冲破我的嘴唇
可以听到鸟声和太阳
云彩向波浪打招呼的声音
诗歌翻山越岭找到我的手脚
它穿过天空发现我的眼睛
明亮象一块少见的玻璃
甚至照出了他的胡须
它两鬓斑白为了今天
有一张喉咙好安排它露面
诗歌流着泪靠在我肩膀上
诗歌站在我耳朵上歌唱――《诗歌》
但渐渐地,生活的压力、年代的嬗变、时光的流转、心境的改变,让梁晓明的诗风大变,他诗歌中的自我也随之转变。他的诗有时显得冷酷、充满嘲讽,迷惘而尴尬,这就是我们要承受的现实,这就是我们要承受的改变:“泥浆在道德的后门口/悄声细语的/把污秽歌唱。”而在《夜》一诗中,他倾诉着心中的黑暗,这个自我拒绝展翅,它听凭自己下坠,唯恐下坠得还不够:我要写一首长诗。一首比黑夜更黑,比钟鼎更沉比浑浊的泥土更其深厚的一首长诗。一首超越翅膀的诗,它往下跌不展翅飞翔它不在春天向人类弹响那甜美的小溪它不发光,身上不长翠绿的小树叶它是绝望的,苦涩的,它比高翘的古塔更加孤寂它被岁月钢铁的手掌握得喘不过一口气它尤自如干涸的鱼在张大嘴巴向不可能的空气中索求最后一口能够活下去的水
诗人的灵魂和生活处于不定和动荡中,他在惶惑中求索:在人生的惶惑中,成熟的石榴最早开口正如秋枫,坚定而后又落入迷茫路在问,河流在问,招展在人头上鲜红的旗帜,那无主的风一遍又一遍把大地拷问是谁在拯救?是谁在指示我们不断诞生?坚定而后又落入迷茫一片又一片代表春天的树叶在我的心中不停地坠落更悲凉、更凄惨,一切都在死去,花死去、鸟死去、太阳和星星死去、春天死去,而宿命稳步走来,要淹没一切,自我陷入绝望:花的死,鸟的死,太阳死后星星去死这样无望又痛苦的归宿啊你总是步履稳重地向我们走来无论我欢呼、忽视、向往或者鄙视你总是如操场上列队的士兵你是威武无人能阻的军队你手持着枪刺向我们走来有哪一个人能够逃避?有哪一个春天最后不被落叶彻底扫尽?
可是“没有希望恰恰萌生出最大的希望”,一首诗,一首长诗,一个真正的自我,一个自我背后支撑着的世界以一首长诗的赐予来给诗人以拯救:没有希望恰恰萌生出最大的希望悲剧在珍视中挂着泪出现但我又怎能逃避我内心这一块冰冻的冬天?那最后一片洁白,而又纯净的白雪的呼唤?无梦的时间将又一次将我渺小的身躯彻底掩埋是这样的一首诗,此刻它恰如一颗星星隐去最后一点光芒它无以题名,它自我的手中正缓缓地写出!
在寒冷和绝望的背后,一种纯洁展现了,那个自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正因为渺小才能感受到宇宙的宏伟,时间的冰凉。诗不再是光亮,而是一种消隐,是在更大的事物中的自我遗忘。正是在这里,我感到了一种蜕变,梁晓明的诗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开阔了。梁晓明变了,但又没有变,他保持了基本的东西,保持了一种旷达的人生景观,但又更加沉潜,他的自我更少偏私,内在的冲突趋于和谐:
我最初的朋友是大海,如今
我最后的朋友还是大海
我低头无语,虚拟的冷漠的悬崖之下
我工作,我狂想,我读书
我努力遗弃幸福这一张马蹄莲的脸
却无济于事,我抬头
我只好默数比我更嘹亮的黑暗和群星――已立之年
梁晓明与翻译家阿九评论家刘翔在杭州,年。
本期编辑:若芜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