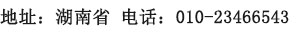弗洛伊德与拉康临床中的癔症/强迫症、男人/女人
作者:吕克·弗雪
译者:潘恒
我将重述弗洛伊德-拉康式的神经症构思的主要思路,以便澄清它们与性别差异问题间的联系。如我们所知,通过隐喻原则(即所谓的父性隐喻)——一个遭受压抑的能指(母亲的欲望)被另一个能指(父之名)所替代,拉康扩展了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
不过,不要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此概念。重要的是要指出父性隐喻根本不是一个跨越性的阶段,也就是说并不能用它来划定出跨越前的阶段或跨越后的阶段。
在主体诞生前,隐喻能否实现已见分晓。周遭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存在此种隐喻主要取决于父亲和母亲的主体性位置。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个体性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在其与享乐、潜在症状以及焦虑之间的关系中主体的自在程度,换言之决定了其神经症类型。病理维度、过度的痛苦因方向错误的隐喻配置而产生。分析能够根据言说所建立的链接来辨识出这些问题,从而进一步地引导某些享乐位点的定位并通过压抑的解除来产生一种补充性建构(将加强隐喻的建构)的可能性。
父性隐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底——我们并不是从病理学意义出发而是根据结构意义来谈论神经症的。此种隐喻的存在限定了神经症,而其缺位则意味着精神病(同样这里的「精神病」一词指的不是病理学,而是结构,也就说它既可以处于健康状态亦可以处于病理状态)。
结构是一种函数(从fonction这个词的数学意义来说),组织了主体的整个生活。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些元素以便把握两大神经症类型各自的动力学:
(1)简要回顾父性隐喻
正如上文中所述,孩子能够脱离“化身为大他者欲望的能指”这一幻想是很重要的。
虽然孩子在其“作为阳具”的意图中受挫了,但是它将滑入一种“有阳具”的辩证法中:如果它不可能完全或排他地作为大他者缺失的能指,即阳具能指,那么这个能指可以被拥有。
孩子将从化身于想象层的阳具(φ)滑动到阳具的另一项:在符号层面上拥有的阳具(Φ)。
可是,“作为阳具”和“拥有阳具”总是共存于神经症中,并且伴随着一种介于(激发各种野心的)作为想象型阳具的全能感和(控制欲望的)拥有符号型阳具的贪欲之间的微妙联系。
(2)神经症中的意谓(lasignification)
对于神经症的临床,父性隐喻产生了一种本质效果:任何意谓都是阳具性的。
其实,在神经症中之所以任何意谓均是阳具性的,是因为神经症的至高价值(组织了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正在于由阳具型缺失所构造的大他者的欲望。无论主体的行动是在于尽最大可能脱离阳具还是永久地要求得到它,阳具都通过欲望指引一切行动和渴望。阳具,作为空或缺失地点的能指,组织了整个欲望空间。阳具型客体相继而来,一个相比于另一个获得价值。这种价值结构相应于意谓结构。因此,意谓密切依赖于这种价值逻辑,而这种价值逻辑仅因阳具逻辑而存在。
(3)对父亲的爱与符号型债务
下面,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父亲成了孩子享乐之障碍,为何孩子爱父亲?
父之名是一个能指、一个能指集合、一个证实父亲的符号性登录的能指网络。通过禁止、认同型特征、理想、定位等形式以及建立意谓秩序,父之名在话语中留下了痕迹。
符号父亲认证了乱伦禁忌,并且为了设置乱伦禁忌而使用“想象父亲”这一支撑物(符号父亲不能简化为想象父亲)。
和一切享乐关系一样,孩子与母亲的乱伦关系产生焦虑。因此,作为乱伦禁忌的担保,符号父亲使孩子免于此种“母子融合”的痛苦。由此产生了对于父亲的符号债务。此债务与救孩子于“融合的虚无中”有关,并且部分源自于对父亲的爱。
神经症的许多成就都出自于此债务,就好像它们是一种偿还。然而,这一偿还是无止境的,因为符号界是无价的。
因此,父之名在能指范畴中代表着符号父亲的登录。它意味着主体位置和能指位置之间的交互关系。
父之名为符号阉割署名,而后者构建了以阳具为基础的价值系统。
(4)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
必须要跟随拉康来区分这两种动因(instance)以便把握神经症的焦点问题。
理想自我在阉割之前其主导作用并基于一种想象的模式。它对应于这样的事实,即作为对于大他者而言的阳具,并相应地产生一种与此事实相关的全能感。
自我理想则既涉及享乐的追还又是对阉割的承担。因此,在大他者欲望的效果中(主体据此理解到自己并无唯一性,即阉割)以及在因接受符号秩序(父之名所建立的符号秩序)而划定出的强制性界限的尊重中,自我理想以自身的理想性实现的方式出现。
这种理想总包含着“要付出代价”的观念,以便达到和维持这样或那样的目标。“要付出的代价”通常会是这样的:
—对于强迫症而言,以努力和牺牲为代价(刻苦学习、认真负责或艰苦地工作);
—对于癔症来说,如果癔症曾经被置于阳具位置的话,那么分配给她的目标总缺少某种能授予其以阳具地位的品质。因此,她总处于失望中。
举例来说,小男孩经常想要成为消防员并爬上高梯。这是一种全能感的实现、一种联系于理想自我的想象型幻想。长大后,此种理想自我式的愿望将持续存在并同时因构成自我理想的阉割作用而有所收敛:男孩将努力学习以便获得学位。这让他能成为消防员营房里的一名下级军官。然而,这意味着他要自我约束以免越过像父亲一样的上级并在其工作中执行父亲的方针。
在神经症的临床中,区分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是极为关键的。这要求我们能认识到在话语中想象层面(理想自我)和符号层面(自我理想)是互相交错的。
再举一例。一位分析者在金融业中取得成就。由于家族传统,他认同于父系血统并顺利通过了后来的高等专业学校的入学考试。虽然他通过努力工作为阉割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这对于还债而言总是不够的。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自我理想的维度。在别的念头中,通过蔑视父亲的某些能力,他部分地拒绝认同父亲。他会表达出其俄狄浦斯式的攻击性。基于想象型胜利的主题,这一攻击性使他萌生了在拳击比赛中获得巨额报酬的幻想。这里他则处于对理想自我的憧憬中。
简要回顾之后,我们试着理解两大神经症的动力学。
(5)强迫症
(A)临床简介
由于药物难以缓解其消沉,这位病人进入了分析会谈。在消沉之初,病人如是说(下文引号部分是病人的话):
“疲劳引发了问题。一直以来我的状态都不错,过着正常的生活。我和妻子相敬如宾,没有问题”。由于对欲望的安排与取消、主体的机械化,后来他说虽然和妻子工作于同一会计部门,但是已同其各居一室。“没人认可我的工作,我也不再认可自己。我觉得当时我用背部的阻滞感以及使我无法做事的麻痹来表达这种感受。我遇到障碍了,这就是起初的状况”。通过这种阻滞现象,雅克提出一种隐喻性的无意识表现形式:“由于疲劳,我不再能跟得上节奏了,没人留意到这点…”。这里,可以发现他在寻求大他者的认可。然后,他说得:“那次搬家太累人了,令人筋疲力尽。太多活了,没人能理解,我累瘫了”。在对“过度累人的搬家”这点进行询问之后,他详细地说道这次搬家是处理岳父家的家具。他从岳父手里「以正常的价格」买了这个房子,并象征性地付了手续费。我们注意到在和岳父一起搬家时他消沉了,而这个房子可以代表其“一系列梦中的房子(在其受压制的话语中所浮现的欲望)”。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他有如下联想:“早晨会有数字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晨醒来脑袋里都会有个数字,比如。然后我被迫要做些计算,比如乘以11”。这里涉及到计算狂、心算症状,试图计算出价格。“我经常这样反复思考…比如,对于父亲的离世: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我并不了解他,他总在出差。我妈妈既当爹又当妈。”娶了他女儿之后,又获得了岳父的房子。这里涉及到强迫症状与父亲之死间的关系。对,这正是强迫症的逻辑,可清晰地表述为此:得到主体所欲望的阳具型财产召唤了亡父并激起各种症状。
(B)理论部分
(a)母性诱惑
母性诱惑使阳具的位置呈现为“作为阳具”的位置,越过了“拥有阳具”的逻辑。多亏了充分的父性力量(换言之,母亲指明了其欲望的另一地点),否则会完全吞没孩子。语言环境使孩子浸泡于“化身成阳具、爱的英雄”等可能性中。可是,幸亏孩子不能填满她,幸亏母性欲望尚有欠款,否则孩子难以得救。
(b)召唤“父性欲望”
因此,要求助于父亲、父性欲望、父亲的显现。此处“父亲”一词仅意指某种对母性欲望的定位,可以使孩子脱离母性欲望。作为隐喻的父亲是抽象的表述,可以从“爸爸”那儿获得支撑,甚至完全用不着“爸爸”。文化知识或工作也能很好地充当“父亲”的位置。混有俄狄浦斯性质的母性欲望将指出许多人物,以至于某个作者或老板都可作为父亲的象征。通常,父性欲望将被一个或多个凸显母性阉割的人物所支撑。
面对召唤,父亲未必作出回应。在强迫症结构中,对父亲的召唤则遭遇了相对的沉默。
由于缺少来自父亲的欲望标志,将使给予主体以一种符号性的抽象物或非现实性。虽有法则的父亲,但无血肉支撑。这是爸爸缺场中的父亲,是?图腾与禁忌?中残留的父亲——虽死而加倍在场的父亲。
(c)对欲望的影响
强迫症的符号父亲将给想象父亲刻上它的印记,更为常见地是给竞争所引入的想象维度的一切关系打上烙印。
我们已经指出强迫症的想象父亲——不够有欲望力的、不够竞争性的、不稳固的父亲——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我们已经提到这种不稳定性增强了符号父亲的力量:死亡的父亲。
对于强迫症主体、对于任何主体,欲望就在于使母亲的原初俄狄浦斯式欲望产生回响。“欲望母亲”使主体进入与父亲(想象父亲)的竞争关系中,并使主体询问后者(符号父亲)的死亡。因此,在这种竞争中欲望,意味着召唤父亲的死亡、其消失——这样的情况使得想象父亲与符号父亲混同在一起。
欲望与谋杀紧密相关,谋杀又与幻想着乱伦禁忌的担保人的消失密不可分。在这里一种混同运行着。欲望召唤与亡父相关的符号父亲。这里,一个初步的滑动使涉及想象父亲的“父亲之死”显现出来。第二个逻辑滑动——作为语言的效果——使想象父亲移动到符号父亲:如果想象父亲——由于它想象性地支撑了符号父亲——死了,那么符号父亲也同样死了、消失了,从而使主体听任母性大他者享乐的支配。正是强迫症的这种混淆极大地限制了其行动,总是将行动拖延至翌日。
(d)欲望、需要和要求;控制与肛欲性
从这一欲望所代表的极端危险出发,拉康将强迫症的欲望确定为不可能的欲望,并提及一种无能状态——在其中强迫症主体欲望着大他者却不毁坏大他者;又由于欲望是关于大他者的欲望,强迫症因此毁灭自己的欲望。于是,危险的欲望最好通过被缩减至需要行列以及诉诸于要求等方式而被取消。
需要——作为欲望的替代品——将主体降格为需要的机能、使主体机械化并以此来安排主体。强迫症的迫切需要避开了竞争的领域、由他者来满足需要的、严格的无第三项的二元领域。需要成了纯粹的机能运作;他废除了欲望。
欲望虽然被修饰成需要的形式,但是它仍能破茧而出、发酵出来或强制性地影响主体。于是,对欲望的压制通过另一途径发生:控制(欲望)。
另外,“控制欲望、控制冲动或欲望的浮现”利于构成一种有关享乐的独特源泉:具有肛欲源头的控制型享乐。肛欲性——作为表达控制感的古老而又优先的地点——受到召唤并与思想一道经历色欲化(érotisé),其特征主要为:控制、扣留(潴留)、保存、收集、排出、毁坏、整洁(作为对粪便客体的享乐趣味之反应形成)、卑躬屈膝(掩盖了施虐之恨)。在强迫症的情况中,这种享乐甚至能超越生殖性欲:肛欲享乐替代了欲望;微末的生殖享乐被撤消,因为它引起了太多欲望,而欲望则引起了焦虑。故而,对肛欲对象(a)的享乐成为欲望的替代物。
在用需要撤销欲望的同时,强迫症还要求得到大他者的认可,尤其是涉及到其工作或牺牲时(例如,上文中的个案)。当此种认可的要求涉及职业范畴时,它表现出强迫症所固有的矛盾双重性(l’ambivalence)。这种矛盾双重性意为既渴望得到其等级制度的认可,又偶尔严厉地批评它,就好像在顺从权威与攻击它之间建立了一种绝佳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他要求着一种授权——对其欲望的授权。可是,此种对欲望的授权又会多少带上一丁点儿负罪感,若不至于过多的负罪感的话。
然而,即便是强迫症中最为微妙的策略仍不能根本上撤销一直坚挺的欲望。
(6)癔症
为了引入癔症的问题,我刚才讨论了强迫症的问题并强调它发生于一种原初的符号范畴中。然而,癔症则更多展开于从想象界引入的范畴中(目光、诱惑)。
(a)母性诱惑
在癔症的抱怨中存在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涉及母亲的爱:要么是缺乏的,丫么是不充足的。
与强迫症涉险于母亲对他的阳具化或对象化中相反,癔症则不是作为一个客体被投注,而是受到了母亲的自恋型投注。
让我们听一下一位癔症的话语:
“妈妈让我学马术。她从不来看我。当我赢了比赛时,她总是很惊讶,就好像我的胜利是件怪事一样。因此,我为胜利犯难。幸好,我可以和爸爸一起骑马溜达。这些构成了美好的回忆…”。还有就是:“她觉得我啥特长也没有;长大后,她怨恨我,就好像我违抗了她,就好像我无权自己做主一样。”再有就是:“要是我的事超出她的掌控,她就会不悦,仿佛她要占据我、控制我,而我不能为自己而活”。
瞧,这就是自恋式的母爱,彷佛女儿是她的一部分且不能向往自主一样。
事实上,母亲更倾向于自恋性地投注女儿,把女儿当成镜中的自己,并将女儿同样视为“缺乏阴茎者”。这就是女性对等性——女儿倒影着母亲小时候的样子。
孩子与母亲间关系的此种特征来源于一种润色后的竞争性。母亲将自己与妈妈的竞争关系移位于孩子身上。这种竞争以及暗含的指责对孩子来说代表着阉割;因此,和强迫症并不会暴露于其中相反,癔症则在母性自恋中经历着监禁。这种监禁的力量又因携带阉割的任务而翻倍。癔症自觉受困于竞争型母亲的魔爪中。
面对如此安置的关系,要想从母性的自恋式控制中抽身,孩子必须使其存在阳具化,觅得一种想象型构造来支撑大他者的欲望。
孩子的阳具化通常优先借助镜像之路,通过大他者的目光来把孩子构筑成理想(理想自我)。癔症的一个关键性锚定点正存在于此:她必须成长于此目光中并在这种欲望中实现自我建构。诱惑也扎根于其想象化的或视觉性的成分中。癔症的阳具化将运用这一模态,因为就这点而言它是最有效的:目光指出了阳具的地点。因此,“使自身阳具化”以便支撑大他者的欲望并脱离大他者自恋式享乐的控制。
(b)癔症(主体)的父亲
癔症将召唤来自父亲的抱有欲望的目光。对于结构的形成而言,其目光的作用会使效果显得理想。
当强迫症不断被送回符号界时,癔症的魔力会过度想象化并提出一个等式:阴茎=阳具。语言环境利于孵化诱惑和目光的游戏。与强迫症中的亡父相反,癔症中存在着父性欲望的表达:用一个生硬但简明的方式来说,癔症的父亲是一个“勃起(bander)”的父亲。
癔症的第一个男人(父亲)以欲望携带者的方式出现在话语中。由于癔症的父亲抱有欲望,准确地说由于其欲望得到了孩子的定位与辨识,因此他与强迫症的父亲截然不同。如此一来,孩子将和父亲进行冲突与爱的交易、以及认同于父亲的欲望对象或直接认同作为欲望者的父亲。
这里,可以在癔症中定位其欲望的两种基本性质:一方面,癔症试图以“其色欲化所激起的欲望中的客体(她)”这一方式来把握自己;另一方面,这一事实——癔症借助这一欲望来想象性地把握自己——将通过召唤“她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方式使主体质询欲望本身的根据。癔症虽挑起欲望并审问它,但并不以此为乐。
(c)癔症与目光
可以说癔症并不缺母爱。令其痛苦的是母爱并未认出她的价值(通过大他者的目光所获得的价值)。
癔症力图获得这一怀有欲望的目光。为此,她将诱惑、询问并表演。她剥夺了他者的安宁以及欲望与否的可能性。她迫使他人注视她,因为这是其生存的条件。此种控制的企图有时会拥入并激起负反馈。
为什么“目光”之路获得了优先性呢?可以说那是镜子阶段中能指登录的优先道路;也可以说为了脱离想象性登录的不牢靠性,癔症所寻找的正在于此。
为了挑起并苛求他者的目光以及在此目光中获得关于其自身存在的回应,癔症不得不成为演剧症、做作狂和过度表现。
(d)追还(revendication)、不满足
癔症询问欲望,追还“对阳具的拥有”并同时宣告阳具样品为无效。
不过,癔症朝向“阳具想象化”的运动是先于此而存在的。癔症设想出一个要到来却从不曾生效的阳具客体。于是,她可以要求收回它。
与强迫症对“作为阳具”的乡愁相反,癔症是一名“志在拥有阳具”的战士。
然而,追还与不满足是不可分地:要想追还持续存在,必须要有不满足来作为支撑。因此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游戏。正如拉康所说,癔症的欲望是不满足的欲望。
(e)癔症和揭发(dénonciation)
癔症揭发“阳具秩序”。这里该如何理解阳具秩序呢?一个纯粹的“阳具中心”系统给两性分配了一个明确的任务和技术规格。这就是所谓的“性化”。这里涉及到欲望的“能力规范”,不过还须接受它持有一种假装(semblant)的、虚设的、仅为提议的特征。
远非灵活地顺从这一秩序,癔症一方面忍受欲望和产生规范的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将这种状况当作荒唐的束缚。换言之,如果根据癔症的证言她不信任这一秩序,那么这种揭发性的举动表明她完美地钟爱着“不容任何假装”的男女结合模态。总之,这掩盖了一种内在的浪漫主义。
“癔症型揭发”的另一形态存在于所谓的“用归谬法证明”中。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对手。用一位抱怨丈夫的女性来举例说明:
“我的丈夫把我当作病人。他希望我是一位家庭主妇,而我不想这样。为什么男人们总要这样呢?就像我妈一样,她不愿意我继续学业并且总是间接地指责我的家政情况。我又不是女仆。我受不了这些所谓的好女人们。她们操心的事儿令我厌烦。您瞧,有一天,他(丈夫)照常邀请了许多朋友。我就让他看看既然我是病人,那我就躺下,反正我就说我病了”。在上述情况中,她玩消失。这使他丈夫进一步地认为她生病了。还有一次,仍旧同一种“揭发形态”:我花了两小时来给客人们做饭。我累坏了。上桌时,我一言不发”。在过度顺从这一秩序的同时,也就是说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她接连用了两种策略来怼假定为丈夫所代表的阳具秩序。这就是“用归谬法证明”。
(7)“癔症-强迫症”二分法
流传着两种无疑太过简单且未经充分讨论的定论:
第一种定论认为癔症=女性、强迫症=男性。然而,纵使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况,它也明显是不成体系的。
第二种定论认为神经症必然且只能结构化于癔症或强迫症模式。这一教条没有考虑到两种神经症能够链接于一种微妙的辩证法中。
乍一看,由于社会效应,男人通常会获得强迫特征,而女人显然会获得癔症特征。不过,严格来说,特征的获取只不过覆盖并滋养了结构。对于所谓的社会特征,举例来说,可以是爱在家修修补补的细心男人、易激动的、富有表情的、爱幻想的女人。
至于结构本身,它涉及的是某种与阳具间的关系,比如癔症中与阳具的想象化关系、强迫症与阳具的关系则是以亡父为参照的危险关系。唯有这种关系才能定义癔症或强迫症场域。虽然结构容易将就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特征,但是它不能定义结构。
在社会或文化层面之外,最初由于性别间的解剖差异及其在性别中所产生的反响,对于女孩来说容易进入癔症道路,而男孩则踏上强迫之路。
这样的倾向取决于来自主体方面的混同,也就是说将阳具和阴茎置于同一层面。阳具是大他者欲望的能指。主体从“作为阳具”的辩证法进入“拥有阳具”的辩证法(拥有阳具以便确保自己爱的专利权)。正如我们所澄清的,阳具是非镜像化的,没有形象。不过,通过想象化的效果,这一能指可以化身为一个客体。自孩子出生之时起,就存在着这一客体,它已准备好代表这一关于缺失(在场或缺场的属性)的能指。此客体正是阴茎。可以发现:对于孩子间的区别来说,这种解剖学特征成了唯一的可能。这种区别是相对于一种“拥有阳具”的逻辑来说的:男孩有它,女孩则没有。
故而,(关于阳具)的符号阉割将仿效解剖上的差异:这一混同意味着“拥有阳具”的辩证法将部分地联系于阴茎的在场与缺位。于是,在可浮动的范围内,阴茎被晋升至阳具行列。
因此,相对于遭贬低的女孩所处的不利条件,男孩倾向于被过高估计:这涉及到性别间的解剖学差异所产生的精神结果。
受周遭话语的影响,女孩易于将阴茎的缺位混淆于阳具的符号性缺失,换言之想象缺失的客体。
癔症一方面将以某种替代形式(想象化)来追还缺失的客体;另一方面,通过证实“即便配有阴茎,男人也缺阳具”揭发此种差异导致的不公、检举阳具中心主义。
至于强迫症,他通常是男孩,因为他要同大他者的吞没之爱——这种爱部分地与母亲想象自己的阴茎这一倾向并以此来回应其阳具缺失有关——打交道。于是,由于配有“小管子”,男孩因过于毗邻母性欲望的客体而自觉受到威胁。
由于拥有阴茎,相比于对缺失的想象化而言,他更多陷入因与阳具、母性缺失的能指邻近而引起的困难中,并伴随着成为母性享乐的专属客体之风险与焦虑。
如此一来,性别间的解剖学差异使男孩易感上强迫症,而女孩子则易染上癔症。不过,要让情况发生倒转的话,语言环境只需偶尔有区别地分配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能指即可。
可是,要理解女性更为必然地进入癔症以及男性走向强迫症,“重提男孩与女孩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某些差异”是妥当的。
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弗洛伊德那里,小男孩处于这样的系统中。在此系统中,最糟糕的“阉割危险”限定了欲望。于是,男孩的欲望构成了危险,并且“控制已降格至需要的欲望”确保了一种可以对抗阉割的担保。
对于男孩,可以看到:正如对于强迫症那样,欲望均构成了危险。于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阉割焦虑使男孩易感上一种对欲望的强迫式管理。
在弗洛伊德看来,女孩所拿到的牌极为不同,因为对解剖学差异的确认证实了一个器官的真实缺位,因此无法对其施以任何威胁。无阴茎,虽导致无阉割焦虑,却进入一种追还中。于是,远不像男孩那样遭遇一种迫使其抑制欲望游戏的威胁,俄狄浦斯中的小女孩被推向了诱惑场景:诱惑父亲、激起男性欲望,以便通过孩子来获得关于阴茎缺位的赔偿。
因此,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女性俄狄浦斯预先导致了癔症型的欲望星空。
拉康的观点
鉴于母亲乱伦式地靠近孩子,拉康的视角指出了母亲的威胁性,并颠倒了经典的弗洛伊德式的配置。
一开始男孩与女孩将建立一个与怀有欲望的父亲相关的神话。父亲通过欲望构建了一种注定要使母亲丢开孩子的真正渴望。
正如结构和时至今日的社会依然要强加的异性恋倾向一样,父性的回应模式清晰地决定了女孩走向癔症以及男孩走向强迫症。
事实上,色欲化易于发生在父女之间。伴随着支撑想象的全视目光,女孩将自身想象成有诱惑性的父亲所欲望的客体:要使父亲看到自己。父性欲望,无论使幻想出来的还是真实的,都使女孩免于母亲的吞没。
相反,对于男孩,与父亲之间的色欲化关系则极为罕见。和父亲的关系将更多带有想象性竞争的色彩。由于迫使他约束欲望且接受规则,这会使孩子处于死掉的位置;相伴而生的是极强的超我,如同指向男孩的母性欲望那般具有严苛性。
以上就是一些试图解释女孩的癔症化与男孩的强迫化的观点。可是,我们并没有提到:正如“每位改变既定结构的新生儿”一样,这些被欲望的形态会因时因人而变化。简言之,位置和欲望是活的,而非固定的。结构仅是陈述于既定时刻中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
(8)结论
我想,在结论时刻说点儿关于标准夫妻的事是适宜的:癔症-强迫型夫妻。
如果它是夫妻的标准模型,那正因为上文中所提到的女性的癔症化预设以及男性的强迫化预设。这样的条件必然促成癔症-强迫型夫妻的普遍性。
癔症召唤、刺激、询问并控诉欲望。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真正的欲望信仰中得到支撑,对此感到得意并从中自我估价。此种受到欲望的活动将牵扯到主要当事人:配偶。然而,配偶因其性别而极有可能具有强迫症结构;因此,其所北京中医治白癜风医院北京正规医院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