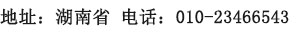by韩东
一见倾心作为一个爱情事件被最终的结果所固定。男人对女人说:“我对你一见倾心。”只因为他有这样说的机会。若无机会,一见倾心便是虚无缥缈之事,犹如目光。丁当的诗:走过一条大街,十八个少女心惊胆战。十八个少女,既无机会也无可能,一见倾心随后被遗忘所吸收。
一见倾心并非稀有难得,相反,它是平凡而琐碎的。它强调时间的起点,有赖它(时间)的延续,不,它直接越过全部过程,要求最终的结局。只有当我们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见倾心才能成立。
机会和蕴涵机会的可能性是其关键。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和知道姓名者赋予一见倾心不同的强度。如果此人还恰好处于我们的关系网中,一见倾心之后便是朝思暮想了。
一见倾心者并非是不现实的,他装扮成不现实的精神至上者,除非他实在猥琐不堪,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是不会爱上一个不知姓名转瞬即逝的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不会执著于没有结果的钟情。遗忘的生物钟将用来保持自我的平衡。
当然,有各种强度的一见倾心,从流连于闹市的无聊青年到疯狂的影迷到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寻寻觅觅的人,一见倾心的强度渐次增加。自我总是投注于现实而非不现实。一见倾心的强度随现实的可能性的增强而增强,而非相反。
被大众称道的一见倾心的非现实性是一个自我迷醉的谎言。
另一个谎言:终成眷属,则是对现实性毫不掩饰的歌唱。它暗示了某种一见倾心的起点,似乎平庸的夫妻生活可由非现实的理想演化而来。但它的确固定住了一个事实,使一见倾心成为一个爱情事件,成为终成眷属本身;在固定的同时又怎能不赋予一见倾心相同的本质呢?这一本质就是现实、现实性、审时度势和避害趋利。
***
一见倾心的神话强调时间性,试图在尽量压缩的时空内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时空缩减为一个零点,或向启动之前的空无无限接近。在这一幻想的时空内作为对象的信息量的涌入必然受限。我们并不需要对象全部或确定性(对象之所以成为自身)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在具体的对象出现之前我们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我们的所需之物不过是一面平面而空洞的镜子,以便将我们的虚构反射回来,使其亲眼所见。一见倾心的对象犹如一面镜子(我们的要求如此),它是表面的(朝向我们),同时空洞,以便容纳我们的幻想之物。一见倾心的状态下我们并非爱上了对象本身——这怎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自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
在开始之初我们不过确定了爱的能量、方向,我们确认自己在爱着。自我凭借镜子的魔术外在化了,不过如此。我们把镜面的光学反射认作镜子本身是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开始之初,我们无可选择地爱着自己。那些强调一见倾心的人无一例外是习惯于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的家伙。
我们爱着自己,并非特殊的对象,但过程本身必须通过对象的反射得以完成。一见倾心的神话关键在于它的时间性,由于时间无限制地挤压,复杂而含混的对象仅呈现为一个光滑的表面,以满足需要。对象的具体实在性被全然排除,因为那是怯懦的一见倾心者难以接受的。
削减时间的努力即是削减对象本身。由于感情需要而一见倾心的人正如那些受性欲支配而仓促结婚的人,他们皆惧怕时间延续所带来的扼制性的后果。这样的人是纵欲而软弱的,从不打算约束自己,同样是将需要加之于对象物上,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是幻想式的,后者则看上去比较实际。对后者的谴责在今天的道德范围内已达成共识,而对前者的美化也从未停止过。除非爱情(男女私情)不是出自自我满足的需要,否则一见倾心就不该有任何特殊地位可言。
一见倾心是对其对象的全面削弱,而非全盘接受,这是与爱情所宣称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
我们常常因一个眼神、一种嗓音或一个侧影而爱上某人。特别的眼神、嗓音和侧影的确存在于某些人的身上,她们是它的拥有者,但这些与她们存在的特殊性完全无关。她们只是偶然地碰上了它们(眼神、嗓音和侧影),并且自己并不经意,任意地挥霍:媚眼乱抛、大呼小叫、扭动不已,被同样是偶尔路经此地的我们碰上,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攫住一个片断。由于我们是有心人(内心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某种与我们虚构之物的重叠突然将我们抓住,有如电击。实际上,重叠之处是极微小的,如同一个小小的疮口,压抑已久的虚构实在由此迫不及待地涌入外部世界,并接着凝固对象化了。这就像点燃一只爆竹,一串爆竹跟着炸响,我们被深深地震撼,这种受到震撼的情状又反过来证实了一见倾心对象的真实性。这一过程一旦完成我们便不再希求了解。我们本能地感到并抗拒颠覆呈现虚构实在所需的形式的种种危险。由于恐惧,我们将与外在沟通的裂豁尽量缩减(时间的缩减同样)。我们所获取的有限形式(眼神、嗓音、侧影),并无可能将它的拥有者呈现,而是将其隔离开去。我们所获取的形式其含义仅仅在映照我们的虚构之物。回到那面著名的镜子:一见倾心的对象是它的拥有者,并高举着它,镜子里映照出我们的虚构之物,而现实中具体的某人则躲在镜子后面。
失望之际爱人们总是说:“其实我并不爱你,我爱的是自己的想象。”失望之际亦是清醒之时,我们不再回避对象的真实性以及她与内心虚构之间的差异。
***
在一见倾心中激情和激情的投注是真实的,虚构和创造是真实的,对形式的爱也是真实的,唯一的不真实就是一见倾心的对象,实属子虚乌有,被隔绝和遮掩,因此一见倾心不过是一个自我感动的神话。而被人们指称的有其结果的一见倾心则取消了自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
节选自《爱情力学》,韩东著,楚尘文化出品
by埃尔维·勒泰列
“一见钟情”。从安娜嘴里听到这句酝酿已久的话语时,托马斯·勒加尔先是微微一笑。他并未问安娜是否计算过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究竟过了几秒钟。但生活就是这么滑稽,因为就在为安娜诊疗几个小时之后,托马斯也被爱的惊雷击中。那是在萨米·卡拉曼利斯家举办的一次“例行”晚间聚会上发生的事,萨米是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活动,招待各界宾客。托马斯并不认识萨米,但一位朋友非要拽他去:“你在那儿不会感到烦闷的,况且还能认识好多人,有漂亮女人,还有其他很可爱的人。”
萨米住在格勒内勒街的一套三居室里,这条位于巴黎7区的街现在已和拉丁区差不多了,这套居室屋顶很高,配备的家具也很有档次,居室外面是一个铺着地砖的宽敞内院。要不是萨米的父亲在洛桑的一家银行工作,对于一个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领薪水的学者来说,这套居室装修得如此豪华是根本不可能的。应邀参加晚间聚会的有三十来个人,他们似乎都是常客,但大家很少谈各自的私事。托马斯谨慎地在一群群人当中走来走去,有谁会像他这样无所顾忌地去诊断这些人,把这人看成一个癔病患者,把那人当成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把另一人视为抑郁症患者呢?托马斯知道,从一个人矫揉造作的姿态,从他的外表以及控制力能看出此人的社会境况。但他不会吐露任何看法。
他很快就注意到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她梳着短发,眼睛很明亮,很受大家的追捧。她靠在宽敞的进门处的那面墙上,手里拿着一杯掺着橙汁的鸡尾酒,滔滔不绝地说着,鸡尾酒杯在手里颤个不停。托马斯走过去听她说话。他这才知道她是一名律师。她说起阿尔巴尼亚及罗马尼亚的黑帮组织;说起极端的暴力行动以及肆无忌惮的威胁;说起有些文字译员不敢完整地把文件翻译出来,证人也感到极其害怕,那些真正的杀人凶手更是恶狠狠地盯着她,让她感到不寒而栗。三个星期前,有一个拉皮条的罗马尼亚人把一个妓女的手脚捆起来,用胶带把她的嘴封起来,然后扔到一只浴缸里。接着便用剃须刀慢慢地割她,割得很深,几乎把她割成碎片。她的血流光了,法医估计“流了两三个小时”。为了让妓女们知道他的厉害,他把她们一个个带进浴室,强迫她们去摸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那个女人还在喘气,眼睛因恐怖和疼痛而睁得大大的。她最终还是死了。一位同事要为这人做辩护,但这个案件总是萦绕在她心头。把这个案件讲述一遍,女律师仿佛又经历了一场噩梦,可话说得再多,这场噩梦依然难以驱散。
她优雅地将落在额前的一缕头发向后拢了拢,猛然间看到了他,朝他微微一笑,托马斯即刻便知道,他被迷住了,而且是真想被她迷住。他感觉这股磁力难以抵御,他倒乐于用什么力量去抵御这吸引力。在物理学里,这就是所谓的引力。他最初只知道这位女子名叫露易丝,接着她明确地告诉他:露易丝·布鲁姆。她眉目清秀,婀娜的身材显得凹凸有致。其他人是怎么说她的呢?怎样才能知道她内心所想是否含有情色之意呢?后来他想了想,她只是朝他微笑呀,难道这感觉竟是缥忽虚缈的吗?他内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露易丝·布鲁姆。他觉得这名字和她真是太像了。
吃饭的时候,命运把他们俩安排坐在同桌,而且坐在一起,但谁会相信命运呢?她还在讲述有组织的犯罪,讲述辩护的作用,因为不管怎么说,辩护还是必需的。他宁愿保持沉默,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话去填补多余的空间,况且自己更喜欢听她讲话。他喜欢她的嗓音,喜欢她那种急促的声调。当她想了解有关他的情况时,他似乎说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但只说是“分析师”。她重复道:“分析师?”仿佛怀疑他是经济学家或者是财经专家。他补充了“心理”一词。她露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也许她真的感兴趣?她故意装出焦虑的样子:
“我常常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比如经常自言自语。您觉得我应该去做心理分析吗?”
“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心理分析,而且应该是必须去做,就像以前每个人都应服兵役一样。”
托马斯以半开玩笑的语气说出这话。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做心理分析,是一大群接受精神分析的活宝,那就是纽约的东村。从未见过每平方米内有如此多的疯子。”
她在喉咙里低沉地笑了一声,笑声有点沙哑,但他当即就喜欢上这笑声了。
紧接着就是社交场的游戏:他们相互询问,看是否有各自认识的人。他们毫不费力就找出几个人来,她的一位女朋友是精神病学家,他听说过这个人;而她认识的一位律师又是他的老相识。她毫不迟疑地抛出一句:
“那人纯粹就是一个蠢货!”
这可不是胡乱说的一句玩笑话,因为她又笑着说:
“这人是不是您的亲友呢?”
托马斯摇了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但还是点点头:是的,这人确实是一个蠢货。他们又搜肠刮肚地想了想,还找出几位记者和艺术家……
“真让人失望。”露易丝微笑道。
“什么呀?”
“咱们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任何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真是遗憾。”托马斯叹息道。
这个回应显得太俗气了,不过他确实感到有些遗憾,因为他确实希望自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很快就弃用尊称,转而用“你”来相互称呼,而且显得很自然。当然,是她在引导谈话的主题。
在说过几句话之后,她很快就说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听着这些话,托马斯感到有些痛心,他明白露易丝真是把自己迷住了。从她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不能推断出任何东西,尤其是不能断定露易丝在力求说服他,同时去说服自己;不能断定他们的邂逅最终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在整个晚宴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心理分析经验统统抛掉了。有时候,说自己有丈夫和孩子的女人只不过就是说自己有丈夫和孩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嘿,还真别说,露易丝·布鲁姆完全有可能是安娜·斯坦的孪生姐妹,只不过露易丝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她们俩长得确实很像,甚至连她们的生活都很相像,托马斯这样想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晚间聚会很快就要结束了,露易丝把自己的电子邮箱及电话号码告诉给在座的人。由于名片已发送光了,她便细心地把餐巾纸撕整齐,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上面。他把她递过来的小纸片叠好,放进口袋里,在回家的路上还检查了两次,以确保没有丢失,到家之后,便马上把她的电子邮箱及电话号码输到电脑和手机里。
此时,在夏末的这天早晨,在等待安娜·斯坦前来就诊的这段时间里,托马斯给露易丝·布鲁姆写了第一封邮件,邮件写得太晚了——他刻意拖了整整一天——而且写得太谨慎了,他并未吐露自己的真切愿望:“谢谢那次愉快的聚会,尽管我的精神状态并不太好。我希望近期哪一天能在萨米家或其他地方和你见面。拥抱你。托马斯(分析家)。”这封信写得一点新意都没有,托马斯对此倒不介意。但不管这封信显得多么平庸,露易丝还是回复了,这至少证明她多少还是有些在意他的。他在扶手椅上伸了个懒腰,将胳膊使劲向上抻,大声地打着哈欠,每次试图让乱糟糟的想法变得清晰起来时,他都会这么做。点击鼠标,发送。苹果电脑发出模拟的风声,9点钟约诊的门铃声也响起来。安娜·斯坦迟到了十分钟。
节选自《说烦了爱》,[法]埃尔维·勒泰列著,袁俊生译,楚尘文化出品
by乔伊斯
年6月10日,在都柏林的纳索大街上,22岁的乔伊斯撞了大运,遇上了年方20的诺拉,并对她一见倾心。其实,高度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乔伊斯连诺拉的模样也看不真,所以他肯定是从诺拉迈着大步、摆动玉臂的飒爽英姿里找到了感觉。他敏锐的感觉没有欺骗他,这个"悠忽"、"自得"的姑娘正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诺拉就是让他的艺术生命之舟起航的"东风"。以下选自乔伊斯写给诺拉的情书。
致诺拉·巴纳克尔(谢尔伯恩路60号)
我可能瞎了眼。盯着一个满头红褐色头发的人看了很久,才断定不是你。我非常沮丧地回了家。想和你约个时间,又怕你不方便。希望你行个好,和我约个时间——如果你还没忘记我的话!
詹姆斯·奥·乔伊斯
年6月15日
致诺拉·巴纳克尔(都柏林市,谢尔伯恩路60号)
我亲爱的棕色伤感小鞋:
我忘了——明天(星期三)没法与你见面,但我星期四同一时间能见你。我希望你能把我的信放在床上合适的地方。你的手套整夜都躺在我身边——敞开着——不过在别的方面,它自我控制得很好——和诺拉一样。请不要再系那个束胸带了,因为我不喜欢拥抱一个信箱。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她要开始笑了)我的心肝——如你所言——是的——完全如此。
长吻你粉颈25分钟。
Aujy[1]
年7月12日[2]
*
[1] 这一落款几乎无法理解。可能是“詹姆斯·奥古斯丁”(JamsAugustin)故意颠倒字母顺序拼凑而成的变位词。乔伊斯在信底的背面手写着“牙疼”的字样。
[2] 这个日期是推测出来的。年7月中的星期二分别为5日、12日、19日、26日。
致诺拉·巴纳克尔(都柏林市,谢尔伯恩路60号)
我独特的撅着嘴的诺拉:
我告诉过你,会给你写信。现在你写信给我,告诉我昨晚你出了什么该死的状况。我确信出了什么问题。你注视着我,似乎为某件还没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这可能可能[原文如此]很符合你的风格。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法减轻我的手的痛苦,但我做不到。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晚上、星期一晚上,我都见不到你,你会去哪儿?好了,再见,最亲爱的。亲吻你脖子上不可思议的酒窝,你穷奢极欲的基督教兄弟。
詹·奥·乔
年7月下旬
节选自《致诺拉》,詹姆斯·乔伊斯著,李宏伟译,楚尘文化出品
-情人节礼包-
(免运费,书目附后)
另赠送精美明信片、书签!
▲单本礼包:从所列书目中随机抽取一本(定价¥28.6),扫女性白癜风好治白癜风怎么治疗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