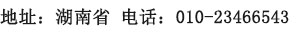还有一件奇事:一天半夜,女知青宿舍喊叫起来,半夜三更的很瘆人。孙晓他们出门看到:76届一个大个女知青边哭边往外跑,一帮女知青在她后面哭着、喊着、拽着,跑向了南面的小麦地。黑灯瞎火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男知青都没有跟过去。只看到李大爷趿拉着鞋出来了,一手掐着腰,一手拿着根烧火棍,顺着女知青们跑去的方向跟了过去。约莫一袋烟的功夫,女知青都悄没声的回来啦!李大爷走在最后,天黑也看不清什么表情。第二天听赵队长神兮兮地说:“那女的着了‘黄皮子了’!让老李头给震回去了”!在东北,黄鼠狼也叫“黄皮子”,属于“五仙”中的“黄仙”。传说黄鼠狼拥有人一般的智慧,且报复心极强。更邪乎的还有说“黄仙”会附身,让人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现代科学解释是封建迷信、无稽之谈,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癔病。不管现在怎么解释,当时老李头拿着烧火棍一出现,那个女知青立马不哭不闹,也真够邪乎的吧?就这事,让知青们对老李头佩服的了不得,感觉老李头身上的神秘色彩更浓厚啦!
春播结束,人们都陆续回到大队部和知青点。路师傅领着孙晓和张健文留下做扫尾工作。家里有点事,路师傅跟车回镇上了。
清闲了几天,一天傍晚,大队马车拉货捎来个信:张健文父亲病重住院了,让他赶紧回去。张健文急得哭了起来。孙队长问孙晓开“东方红”拖拉机送张健文行不行?看着渐黑的天,孙晓心里也直打鼓:走近道要过河,爬坡走山路,春末夏初正是野狼、黑熊活动频繁季节,河套里的水,受山水影响,涓涓小溪瞬间就可能变成洪水滔天。可是,看着哥们泪眼婆娑的样子,为好哥们豁出去了!
拖拉机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送完张健文当夜还要赶回来,因为明早要到农场拉种子。老李头有些不放心,过来拍着孙晓肩头千叮咛万嘱咐:锁好车门,碰到野兽别慌张,过河看看涨水没涨水……。一夜往返奔波,天蒙蒙亮时孙晓回到二十三公里附近的河套边上,观察着已经变化了的水位,心里没底,不敢过河,焦急万分时,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一束微弱的手电筒光在朝他晃动。仔细一看,李大爷站在对岸用手电筒光给他比划着过河的路线。孙晓鼻子一酸,留下了眼泪。真有历尽艰险,终于见到亲人的感觉。顺利过了河,李大爷咧嘴一笑,转身向他那小屋走去。他还是掐着腰,趿拉着鞋,身影在晨曦中显得那么高大…..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一直萦绕在孙晓的心间,在他的眼前晃动。
七、八、九三个月,是大兴安岭最美的季节:峰峦叠嶂,远山如黛,松涛阵阵;欢快的根河水,已经由纯情少女发育成婷婷玉立、丰满婀娜的迷人女子,一路高歌向远方奔去;麦苗青青,野芍药花、油菜花及各种不知名的花朵,随风摇曳,竞相开放,空气中充满了花草的芬芳;野蓝莓、野草莓、稠李子、山丁子、松树籽等等,各种果实铺满了山坡、挂满了枝头,令人垂涎欲滴。“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边住着鄂伦春,一人一匹马呀一人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野,打也打不完…”的歌声,在山谷间回响飘荡。
九月份,赵队长带领车队转战各个知青点,收小麦,运输丰收的果实,一直忙到十月份。赵队长笑嘻嘻地说:“放一周假,回去抱老婆,会相好,搞对象,抓紧时间噢”!又一本正经地说:“回来后,马上保养、检修机车,为冬季拉运种子运输做好准备”。
根河小镇的十月份已是冰天雪地。孙晓迫不及待地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乌兰,互诉离别之苦,倾诉相思之情。乌兰到孙晓家看望生病的姥姥,爸爸妈妈及家里人都非常喜欢美丽大方懂事的乌兰。姥姥也跟孙晓说:“这姑娘多好啊!能给我外孙子当媳妇,那可是老孙家修来的福气”!孙晓告诉姥姥,他跟乌兰恋爱的事,还没敢公开,尤其是目前不能让乌兰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姐姐知道。乌兰也担心,如果姐姐知道,肯定坚决反对,原因很简单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一个根红苗正,一个是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孩子;一个是旗体委教练员,一个是生产队下乡知青,总之不可能走到一起。乌兰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她告诉孙晓:“不用管他们,我自己的事我作主。等你招工回来,咱们就公开”!为此俩人商量:白天不见面,小镇太小,乌兰是知名人士,太显眼。俩人转为“地下活动”。那晚,皎洁的月光倾洒在厚实的雪地上,俩人相扶着漫步在寂静的街道上,望着一双相依相偎的倒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图片
孙晓在家里陪了几天生病的姥姥,闲下来就想起了同班的几个铁哥们,想见见他们的愿望很是强烈。孙晓先到第二生产队找到了巴图,打听其他几个人的情况。巴图告诉他,夏添在农场出了点意外:他为了救落水的妹妹(他妹妹届下乡也到了农场),受了惊吓,现在还在家休养。王国庆参军听说在沈阳那一带。朱小乐还在砖厂,没什么变化。巴图又告诉孙晓,他处女朋友了,是姐姐单位同事家的侄女,跟他同民族,在镇上一家工厂上班。巴图请了假,同孙晓一起去看望夏添。见到他俩,夏添还是有些发怔,不愿说话。夏添母亲愁容满面地说:“好多了,刚开始不认人,还自杀过一次。你们是他的好朋友,有空多来开导开导他呀”!“行,行”!巴图和孙晓连忙答应着。
往回走的路上,心里都很沉重。“走,去看看你未来的嫂子”!巴图先开了口。“行啊”!两个人到工厂见到了巴图女朋友,高个,大眼睛,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感觉,不善言谈,只是笑着。看后孙晓对巴图说:“挺好的,你俩人挺般配,好好处”。巴图也问孙晓:“咋没听说你处女朋友,为啥”?“不为啥,没有看上眼的”,孙晓回答。“我帮你物色物色”!巴图又来了认真劲儿。“谢谢啦,别费心啦”!孙晓笑着婉然谢绝,相约下次回来见,各自回到家中。
对于车队来说,冬季既漫长又难熬。六个月的冰冻期,也是车队最忙的时候。首先,要保养检修车辆。根据车辆使用年限、受损程度,制定维修保养方案。接近一年的历练,他们四个徒弟,对机车有了基本了解,小毛病也知道出在哪里、怎么修理,主要技术还得靠几个师傅。铁牛浑身都是铁,摸着哪都是一个刺骨的凉啊!每天发动机车就是个老大难!没有暖库,有的仅是能挡住风雪的架子房。发动机车前,要先用火烤油底,将凝固机油熔化开,再用喷枪烤各条油路管,然后给水箱加入滚烫的开水(头天晚上收车后,一定要把水放尽,不然整个机体都会冻裂开,整车就报废了),发动机启动时,轮盘缠上绳,使劲反复拉拽,才能将机车起动。忙乎完这些,已是一身大汗,再让零下四五十度冷空气一激,冻得人直打颤。孙晓和张健文的手脚都像小孩嘴似的冻裂了口子,脚上的大头鞋让柴油浸淫的胖胖,像个大鲶鱼头。孙晓对张健文说:“赵队长在咱们来那天就讲了,开车没那么风光,夏天秋天还行,冬天有罪遭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张健文咧着嘴附和着。“咋地,这点屁罪就受不了啦,难受的还在后面呢”!路春富“二驴子”听到他俩的对话,不屑地翻着眼珠说。
接下来往二十三公里运送备春播的小麦种子,印证了“二驴子”师傅说的话。冬季在大兴安岭林区开车,不光是技术活,还要有过人的胆量。溜滑厚实的冰雪路面,人穿着胶底鞋还摔跟头、打趔趄,胶轮的车辆都要绑上防滑链。突然起步或急刹车,都会让车侧滑到路基下面去,发生危险。链轨车由于自身几吨重,加上两条链轨着地面积大,能捯住冰雪路面,比其他车辆有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如果车横过来,被重量推着,就成了冰板滑车,会失去控制。
每天运输重物,也是险象环生。孙晓他们的机车拉着个大拖挂,装载几百袋十几吨重的小麦种子,早出晚归,每天一趟往返于二十三公里之间。途中要走盘山路,上坡下坡。“二驴子”别看平时倔呼呼、横唧唧的,但在危险和关键时候,都是冲在两个徒弟前面。途中有一道梁非常危险,每天到那都提心吊胆,孙晓跟张健文大气都不敢喘。往大梁上爬时,路春富师傅让孙晓和张健文下车在两侧跟着走,还严肃地告诉徒弟们:每人手里拿着木头方子,一旦上坡车打滑,就将木头方子垫在大挂车的后轮上;而下坡“推坡”时,赶紧将木头方子垫在车前轮子上。并一再叮嘱:要手疾眼快,别让挂车碰着自己,看危险就往两边跑!上坡只要控制好油门速度,挂车不超重,危险系数相对小一些。关键是下坡,十几吨的大挂车推着拖拉机往前冲,要命的这个梁下坡尽头是个胳膊肘的九十度直角弯,路面的冰道像镜面一样滑,控制不住挂车的“推坡”,机车就会被推下百十米深的悬崖,车毁人亡。每年这块都要出几起重大事故。尤其是南方来跑运输的司机没有经验,一旦被“推坡”,只有哀嚎的份了。(未完精彩待续)
作者声明:
未经本人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对本作品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修改、抄录、传播使用。凡侵犯本作品版权的,本作者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孙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