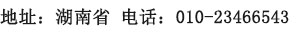老屋前的枇杷树
文/阿哲哥哥
若不是妻子把枇杷采回店里,我都已经忘记了老屋前还有棵枇杷树。女儿把一大胶袋的枇杷装好,说是要送给老师品尝下的。然而我却不看好,学校老师会喜欢这味淡涩口的枇杷吗?
老屋在小龙山,搬离小龙山已经多年了。这栋建了四十多年的土房子在夏雨浇淋下,加上没有人居住,有点漏雨了。昨晚的惊雷暴雨洗干净了通往老屋的小路,老屋前枇杷树上的枇杷也由青绿变成了黄橙。
雨水的洗涤未曾把枇杷上的绒毛洗净,却把枇杷的酸甜洗得有点淡而无味。厚厚的果皮里果肉变得十分单薄,果核却有点坚固。
果核是不能吃的,但是却可以在来年的春天在黄土里长出新的枇杷苗。
枇杷树我不记得它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种的?小时候还没有等到枇杷树上的枇杷成熟,青酸的果皮还是如叶儿般油绿时,妹妹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也会在树底下悄悄尝一下枇杷的酸楚。
心中一直会疑惑:不见枇杷花开满枝,但是枇杷却总是硕果累累?
小时侯,如果遇上有一点风寒感冒,母亲还会用枇杷树上的叶子,刷干净背面的白毛,混一把在大山里采回的草药矮地茶,配一点黑豆,熬一碗水来喝。味道是涩楚如老茶,颜色也如中药般微黄。母亲说喝下便不会咳了,然而效果好像并不显效。
只是想着碗中还有几颗黑豆,馋得流了囗水,嚼在口中,粉粉地,塞在牙缝中必须用枇杷叶水再冲嗽口中的味道。
老屋门口种的树还蛮多,我还是从怀化带回的梨树刚刚长出新芽便被父亲砍断了。因为忌讳梨树的读音。铁树从娄底姑姑那里移栽来的,因为长得太慢,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
桔子树因为生了虫,长得树瘦果苦,经常落得满地青果。唯独这棵枇杷树,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也不长在屋前的正中,偏斜地长在竹林的边上,也不管你们爱不爱吃,也不怕虫咬风吹。
居然由原先的三个分丫变成郁郁葱葱,也由最初的挂果三两枚变得如珍珠聚会般数不过来。天的雨经常夹着雷声,纵然有风吹树弯,似乎枇杷树上的枇杷你不去摘它,就是完全熟了也不见它会落下。
它固执地等待着我们去采摘它。然而老屋有一天老了,父亲都爬不上屋顶去捡修漏雨的瓦片。母亲更是大腿风湿疼痛也不会用枇杷叶煎水做药喝,好像枇杷叶对风湿痛也没有作用。枇杷树却在风雨之后,叶绿成了华盖。
数不尽的枇杷也不管你是否馋不馋嘴它总是及时挂满枝头。
有时候,有鸟栖在枝干上。只听见叫声一片,却不见它们也叼一粒枇杷。大概它们也知道枇杷味变了,变得苦了,涩了。
老了的岁月,流转的枇杷树,果满枝头时如耀眼的黄色珍珠,蓦然回首,忽然一天不见了昨日的光芒。
枇杷落了,落在潮湿的地面,厚厚的一层。
作者简介:阿哲,本名何卫强,双峰县杏子铺人。一个行走在乡村角落里的兽医师,佛教徒。爱好文字,只是源于最初的心,用自已的眼睛发现岁月留下的悲喜印痕。
☆☆☆☆☆
《杏子乡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