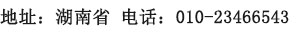康德和笛卡尔,并不是为了德国或法国争夺哲学话语权,才写哲学书的
在形而上学领域,骗子是最多的,而且普通人也难以分辨思想的骗子与真正的哲学家。更有甚者,骗子更容易得逞,因为人们不愿意多费脑筋澄清思想的细节,对于思想本身的兴趣不大。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尤甚。中国民众要是相信什么,往往先会这样想:我信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凡事喜欢走捷径,最好是用的气力最小,得到的好处最大。至于官员,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一方面愿意听到国外多么不好,另一方面愿意听外国人说我们好得不得了,这样的心里是自卑的。还有,信风水,这几天北京城里正在拆除一个有名建筑顶端的“龙头”,也不知道是什么风向,但它肯定与某种不是哲学的东西,有密切关系。
和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心理,我说出来读者可能不信,但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中国民间通常说的“癔病”——这种心理障碍,与迷信巫术之类,有着极其微妙的差异,但却是本质的差异。质言之,癔病是朝向思想本身的,而不是说我想往某件事,这事情得给我带来某种好处。不是的。犯癔病的人,自己和自己在念头上较劲。但这些念头,与任何算计性的事情无关,只与思想的死胡同或者想不开有关,它与天真无邪的念头有关。比如,一个少年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将来会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己彻底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很是恐惧,竟然哭泣起来了,这并不是愚蠢,而是纯粹思想感情本身的诱惑力。它还会以乐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萨特年轻时,认为自己是不会死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会傻到认为自己真的不会死,而是觉得自己不会死,因为死这件事,完全是匪夷所思。如果想得更复杂些,就会想到,死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没人在意你的死亡,如果你想到这种情形而感到绝望,你就当不了一个哲学家,因为你的绝望感是多数人都会有的心情,你这不叫癔病。真正的癔病是精神分裂式的,不是抑郁。精神分裂,就是说觉得无人在意自己的死亡这事挺值得玩味的,就好像接续的念头坚决不替自己着想,这就进入了某种思与想的纯粹性。这就离哲学门槛不远了。
从根本上说,哲学家不仅对于思想本身感兴趣,而且是自己亲自思想。“亲自思想”这个表达有点古怪,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在亲自思想,或者拾人牙慧,或者自动遵循某种习俗,去“和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亲自思想,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不会想了。我是说这样的想,不同于你想办成一件事情的想法,而是纯粹的动心,没贪图什么身外之物。
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和康德是如何亲自想的,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他俩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为了法国或者德国想,没想什么为自己的祖国争光,与同胞也没什么关系,也不想什么个人荣誉的事情,更没想为法国或者德国在世界上争夺什么哲学话语权——这事应该这样看,当他们有这些杂念并且将心事放在这些杂念上的时候,他俩就毁了,而当他俩根本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的时候,这些后来的思想桂冠反而被后人给他俩戴上了。用叔本华的话说,这些杂念都只是在思想的外围。这就相当于你去参观故宫,你只看见了红色宫墙,很壮观,以为看见或者得到了好东西,其实好东西都在宫殿的里面呢。我们没有进到思想的里面,只是围绕外围打转。至于我们中国思想界现在的问题是,在思想的外围打转的思想,披上了思想的外衣,被人们认为它就是思想本身了,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的思路,没有使我们在真正的思想之路上前进一步。
什么意思呢?挺有意思的一个没有思想质量的顽念:作为个人,或者说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比如,我们从来轻视某种突袭而来或者不知不觉涌上心头的想法,而是首先要“正名”——正名不是证明。证明属于哲学与逻辑的一部分,而正名本身,却是在哲学之外的。所谓正名,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分类方法,它一直延续到我们如今的思想界,就是说在真正的思想之前,我们就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区分,比如中国的、西方的,过去的说法,则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只有将这些观念被放置到某个固定的位置上面时,我们才会感到心安理得,要区分出优劣、秩序、尊卑、善恶。当说到思想的时候,从来都不说“我自己的思想”,而是“我们(民族、国家、领导)的思想”,这使我不由想到它们可能就是变相的祠堂里的牌位思想,而且要按照血统和顺序排列出来,如果是还活着的人,则有严格的等级和服从的制度。这种所谓思想,从一出生就是目的性的、计划性的,问题在于它们不是首先经过经验或者实验的证明与论证的过程,完全无视思想的自发性与其他可能性。只有统治者的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市场,就像只有计划经济而没有市场经济。那么,就会出现我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口号政治”现象,而且是数字化的口号政治(过去有“五好战士”、后来有“三好学生”……对于这种形式的被装饰上“思想”伪装的、与哲学没关系的数字政治口号,实在太多了,我们也实在太熟悉它们了),这东西是舶来品还是祖传的?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两者都有。故宫乾清宫上的牌匾“正大光明”,就相当于古代的“口号政治”。但是,对于从来就不曾有政治上的“正大光明”这一事实,我倒是觉得不应该谴责,而应该这样想:其实每个人都有个人私密的自由,但是碍于礼仪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公开给人家看的东西就得让大家喜欢,这也是出于善意。这里已经有哲学思考的苗头了,比如,进一步想,可以假设人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都可能干坏事,这是人的利己本能,所以要限制最高权力。这个想法很残酷,甚至不道德,很小人,但是,假设出现最极端的坏事——这种念头,与假定人人皆可成尧舜相比,更加具有思想的力量,也更符合人内心的真实。
以上,我们的思想界,首先摆弄一堆自己喜欢的概念,独断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然后将这些观念放置到某一个参照系之中,排座次、排地位,这与很多学者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