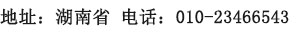年,我为追逐一只珍奇的鸟而坠入深渊。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夏洛特?路德维克?马克西米利安?欧根妮,皇家骑士团中的唯一一位女性获准加入圆桌议会。从姓氏判断她不是英国人,甚至并非来自新教家族,单纯因为出色的技艺得到女王青睐。她淡金色粗硬的长发,柔韧的身体,高傲不屈的面容,身后交叉背负的匕首和弯刀步枪,都饱含浓厚到难以撼动的生的意志,让我嫉妒难忍。对毁灭这份生的意志的渴望,与性欲,与体内的猩红饥渴相交织,使我每日每夜从胃到喉咙都烧灼一样发痛。
在她负责巡视的码头,我装作无意地撞见她。簌簌水声中,体型庞大的联合印度公司货船接连起锚。我向她问好,与她并肩注视水手将猪油运进熔炉间。「比起木柴,猪油燃烧产生的热量要大得多。」夏洛特说,并没有看向我。货船如同弓弦一般猛烈震动,随后飞驰而去,其余小型船只上看热闹的水手们爆发出欢呼。「您该回梅费尔区的住宅去,爵士先生,这里不是您应该来的地方。」夏洛特平淡地对我说,而后转身离开。十月气候已经很冷,但她穿着单薄,深入雾霭中便如一句轻柔的琴声一样踪影消散了。
码头空气里燃烧物气味刺鼻,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白教堂区的恶浊臭味。伦敦空气本已够糟糕,白教堂区尤甚。透过那些恶魔肠胃般弯曲狭窄的巷道仰视天穹,可以看见这城市从无数烟囱里喷出噩梦般的灰霾,礼拜堂尖顶上的十字架也无从辨认。衣衫褴褛的饥饿者渴求一块变质的面包、一条死狗肉肠、一勺点滴油星炒过的马铃薯薄粥;酒鬼醉死在污水中,梅费尔区的先生太太乘马车优游路过时,只拿他们当作鬣狗尸体。街角酒店里有一些穿肮脏马甲、手指粗大的顾客,或者打扑克,或者玩骨牌,还有两三个站在柜台边,慢慢喝杯里剩下的酒。在这里可以轻易找到妓女,穿蓬大纱裙、露出一半胸脯,声音甜蜜如烂熟苹果,可爱的动物。年后某一段时间,我常常在黄昏时分换上黑色衣氅,来这里随意找一个外省的贫穷少女,她有一双杏褐色眼睛和同色的辫子;或者一个大革命后逃离大陆来此、家境破落的高卢女人,或者一个最平常不过的洗衣妇,将她们带入拐角处的阴影中,俯身亲吻她们的脖颈,吸她们温暖的血。成为马洛礼爵士后我不再涉足白教堂区,但那份污秽的甜蜜,令我每每回忆起仍然快乐得唇齿打颤。
披上人类权力外衣后,对体内猩红饥渴无法满足的担忧变得不那么必要——联合印度公司通过私密渠道定期供应给我新鲜的人体。然而,遇见夏洛特之后,特殊的饥渴又苏醒了。我想我对她的嫉妒和钦慕是一体的。我渴望与她成为同伴。十一月初,我了解到她将前往白教堂区调查印度移民的杀人事件。白教堂。我念着这名字。我将再次在这里得到爱人。
在这贫民窟中,一处腥臭扑鼻的屠宰场后,我制服了夏洛特。人类的反射神经终究太弱,即使经受训练的骑士也不堪一击。我将牙齿插进她的动脉,希望使她成为我的伙伴。然而我没有得到她,她的身体对我的拒斥比我想象的更剧烈。她死了。与其说她无法承受我的血,不如说夏洛特借助死亡逃离了我。多么残酷。成为不死者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神的残忍无情。不要逃离我,我孤独得要发疯。我尖叫着,背部舒展开蝙蝠翅膀,腾空去追逐她飞散的魂魄。十一月冰冷的夜气深深沁入肺部,背部双翼推动我在空中狂奔。云在身后飞泻,血红的月亮在身后疾跳,整个荒凉的黑夜在追赶我们;但是此刻,对她而言只有我必须被逃避。从市中心到城郊,视野中掠过三三两两的屋舍,破落的农庄,废弃楼房、染坊、鞣革作坊,诸如此类种种,荒野、秃树、坚硬崎岖的路面,路两旁深厚稀软的泥泞,都与我无关,我一心一意追逐同类。最终还是失去了方向,陷入彻头彻尾的绝望中。她回神那里去了,回到与我所代表的死亡意志完全悖逆的地方去了。
我降落在一座半倾颓的礼拜堂中,精疲力竭,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墙壁的镜框上装饰一排四肢残缺的丘比特画像,有几个连头部都已缺失,捧着装满死海果实的黑色篮子。一尊圣母像从上而下俯瞰我。太孤独了。我捉住圣母像那只石膏做的手,将它在我手掌中捻碎。透过废墟,透过残破的门的骨架,我看到四周都是荒原,连大河也已冻结,填满了船只朽烂的残骸。恍惚间,废墟上走来一支送葬的行列,脸色苍白的男女,车轮载棺材辘辘前行。我看见夏洛特,她黑色薄面纱后的眼睛枯萎无神,一只戴长手套的手紧抓一本黑封皮的祈祷书,另一只手覆在棺盖上;透过玻璃棺盖,我看见躺在其中的也是她,金发飘散在白缎上,双手握住玫瑰。「如今你已在尘世受到诅咒。」她对我露出微笑,牙齿尖锐。
这梦魇般的可怕场面中,一切都怪异地自相矛盾。太孤独了。我无法承受,心中充满对自己的仇恨。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唯一的一场癔病。
后来我永远离开了英国。
赞赏